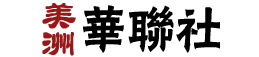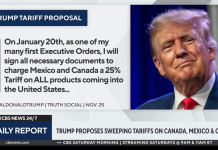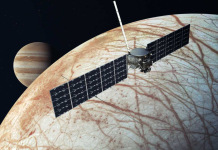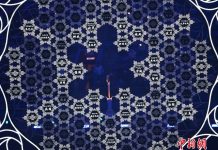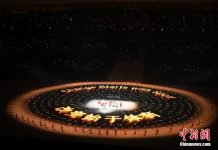中国侨网12月19日电据法国《欧洲时报》报道,2009年回中国定居以来,旅英作家虹影一直维持着“候鸟式”的生活。每年夏天,她都会在欧洲度过。几年前,她把在欧洲的家从英国搬到了意大利,“我不喜欢英国。”她说,英国对她而言意味着阴冷潮湿的天气,不好吃的食物,保守的文化和僵硬的、难以接近的人。
“从圣诞节前一直到3月份,伦敦经常刮大风,特别冷。”在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家,虹影望着窗外被北风吹得碧蓝的天,回忆起12000公里外、那座她生活了九年的城市,“那儿有很多特别老的橡树,风一刮起来,橡树都歪了。每个人都穿着黑色的大衣,举着一把伞,紧绷着脸,从地铁站走出来。伞都被吹翻了。天特别暗。”
这样的伦敦让虹影想起重庆—她18岁逃离的家乡,她留在贫民窟里的童年:重庆的天气也总是阴阴的,一下雨,每个人都举着伞,没有伞的穷人就在雨里奔跑,脸也是绷得紧紧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伦敦很富裕,我小时候的重庆很穷,但人脸上的表情是一样的。”
异国与故乡,现实与回忆,西方与东方……初出国门的女作家在无处不在的文化碰撞中观察着陌生的国度。她在当地的朋友不多,也没有参加任何文学社团,一心一意地把自己投入孤独之中。
1999年,虹影颇受争议的作品《英国情人》在台湾出版。这部小说写西方人的偏见、生活的意义,讲述了一个英国男人与一个中国女人在特定年代的爱情故事。“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肯定写不出这本书。在英国的生活让我能够沉下心来写作和读书,并且深入地去观察和感受另一种文化。”
虽然不喜欢英国,但虹影却非常庆幸当初去了那里,“如果我当时是去了意大利或西班牙,我肯定就完了,成天去享受地中海的好气候和美食了!”她笑起来,“一个地方的不好有时候反而能成就你。”
旅英期间,虹影创作了《英国情人》、《饥饿的女儿》、《女子有行》、《孔雀的叫喊》四部长篇小说。此外,她把大量精力花在了与赵毅衡共同主编的《海外大陆作家丛书》上。
虹影从书架上找出这套2001年出版的四卷本丛书,两册散文,两册小说,一一细数着目录上的那些名字:阿城、查建英、高行健、顾城、严歌苓……她说,这套书,他们编了好几年,和其中的每位作家都取得了联系。“像高尔泰,当时他的东西根本发不出来,我们从他的《寻找家园》里选了几篇;还有张宗子,现在在大陆已是小有名气的散文家,但当时还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
被收录作品的作家多是1980-90年代出国的,虹影说:“那时候国内对这些都不了解,不知道他们出去之后写了什么,所以就需要把海外的那些作家介绍回中国来。”此后,她一直保持着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
记者:在海外和在中国写作,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吗?
虹影:现在和以前不大一样了。网络很发达,大家查资料、看新闻都可以通过网络解决,比如我现在不住在英国,但我也可以知道英国每天都发生了什么,以前就不可能。我认为,对作家来说,在什么地方居住不重要,和什么样的人住在一起更重要。
记者:旅英的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虹影: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简·奥斯丁的作品,但直到我去了英国,看了她住的地方,然后又在英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才真正理解了她的作品。你会发现,全世界是一样的,只要是人,都是一样的。好人也可能做坏事,坏人也可能做好事。人是复杂多面的,一个作家能把这一点写出来就非常好。
记者:有没有考虑过用英文写作?
虹影:没有。第一,我觉得我天赋不够,我能把一件事做好就不错;第二,我不希望找人来代笔,用英文写作的话一般都会有代笔,或请别人来润色。
记者:你1991年去了英国,据你观察,从那时候到现在,旅欧华人作家这个群体有什么变化吗?
虹影:没什么变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拔尖的人,能数得上的就那么几个。在国外很少有人能靠写作为生,大部分人都要做其他工作。写作是一件很艰苦的事,特别孤独,能坚持下来不容易。
记者:欧洲的读者怎么看待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
虹影:在欧洲,中国文学是一种少数族裔的文学,普通读者对中国文学没太大兴趣,更多的是一种猎奇……他们知道的中国文学也多是古代的,孔子老子唐诗宋词……当代的基本没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