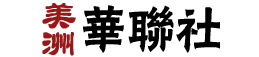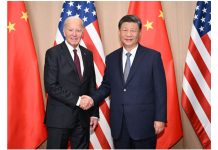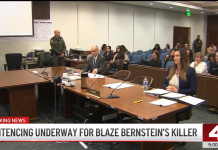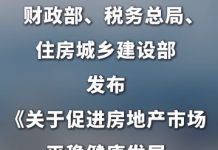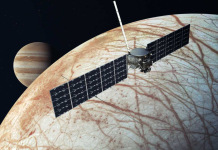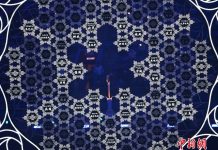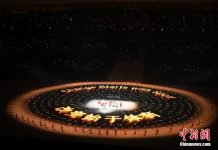媒体报道,被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为国内慢粒白血病患者代购印度抗癌药的陆勇于10日晚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北京警方带走,羁押于朝阳看守所。事件起因于陆勇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于2013年8月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批捕,2014年3月19日陆勇被取保候审,此次抓捕是陆勇已被列为”网上逃犯”。因而案件管辖地实际是湖南省沅江市,北京警方只是协助沅江市公安局抓捕而已。
陆勇在2002年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当时医生推荐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服用这种药品可以稳定病情、正常生活,但不能间断,每盒药售价为23500元,一个月需要服用一盒,因而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根本无法承担如此巨额费用。后陆勇偶然了解到印度生产的仿制”格列卫”抗癌药每盒仅售4000元。印度和瑞士两种”格列卫”对比检测结果显示,药性相似度为99.9%。陆勇便开始服用印度仿制”格列卫”,并在病友群里分享了这一消息。随后,很多病友让其帮忙代购该药品,人数达数千,陆勇为方便交易,先后从网上购买了三张信用卡,并将其中一张卡交印度公司作为收款账户。去年9月,”团购药价”降至200元每盒。另据报道,印度的”格列卫”在印度属于合法的”真药”,但由于该药品没有取得中国的进口审批许可,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假药”。最终,陆勇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查看近几年媒体报道,类似陆勇这种代购抗癌药涉嫌犯罪的悲剧,先例不少,政府监管与立法目的似乎已严重脱节,目前仍难看到改变或纠正的迹象。
我国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构成销售假药罪”。而根据《药品管理法》第48条第2款第2项规定,”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药品,按假药论处”。根据前述规定,陆勇代购的印度”格列卫”因未获得国家主管部门的进口批准,符合”假药”的法律规定。由于我国刑法规定该罪应达到”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情节方能构成本罪,为将通常的制假、售假行为纳入犯罪评价体系(一些制假、售假行为未必危害人体健康,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影响恶劣),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通过了《刑法修正案8》,对该罪名予以修正: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制假、售假的行为,即构成本罪,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由原来的犯罪成立条件改为犯罪加重情节。基于前述法律条款,我们不难看出,立法机构对销售假药罪的犯罪构成、保护对象以及社会危害等均作了系统、科学的规定。
然而,因为《药品管理法》关于假药的认定标准,导致陆勇这类既无犯罪主观故意,又未造成客观社会危害,且未获取不当利益,实质乃自救与互助的”代购”行为,因涉嫌触犯刑法规定而入罪,冤枉且不公平。
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根据《药品管理法》第29条规定,”药品进口,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我们不禁要问,瑞士的”格列卫”可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进口的行政许可,印度的”格列卫”为何不可以获得进口许可的同等待遇?而且,药性相似度为99.9%,效果一样的两个国家的同类产品,获得进口的瑞士”格列卫”价格高出未获进口的印度”格列卫”价格近5倍。作为普通公众,要以何种恰当的理由,才能理解如此巨大的价格差距是合理的?要以多大的包容心,才能认同政府监管部门对这类事涉癌症患者生死的药品审批与价格监管?
或许有人会说,印度的厂家没有向我国申请出口,中国也没有企业或个人申请该药品进口,所以印度生产的该药品未获批准进口当属正常。其实,笔者想表达或思考的重点不在这。重点在于,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其行政职能职责范围内,为何不可以有更大作为?要知道,陆勇们这类癌症患者,皆是因为无法承受药品的巨额费用,才冒着触犯刑律的危险,寻找更合适的”救命之药”。他们这类人的悲哀在于,不铤而走险,就可能会因买不起自己国家合法销售的药品而等死。
法律条文制定的目的之一,应是为了增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这种幸福能否得以按照法律设定的目的实现,有赖于执法者严格而不失灵活的执法态度与思维。而这其中的灵活,应是行政职能监管部门,在僵硬而冰冷的法律条文背后赋予其更多的人性与活力,达到或保持与立法目的高度统一与一致,从而真正实现立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