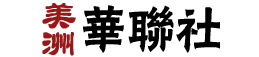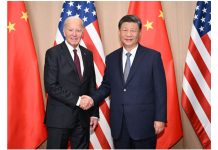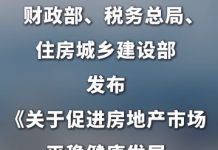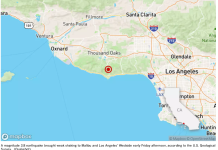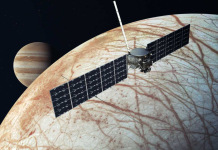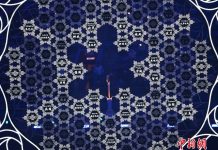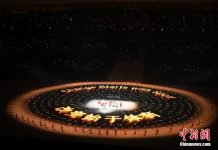几千年以来,中国人认为自己地处’天下’之中央,又居文化之颠峰,具威震四方之武力,天朝乃中央之国,是各蛮夷来朝拜之圣地。不幸,差不多170年以前,几千里之外的西夷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举国上下,又惊又恨,又恐又疑,真不知为何天下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之事。但门开了,就有进有出。进进出出,各式各样,其中进来的有二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另一位是赛先生。起初,大家并不熟悉这二位先生。经过七,八十年的反复,最后,大约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家基本上达到了共识:我们应该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教我们一些什么东西,中国才能从病弱中恢复过来,强壮起来,在世界之林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关于德先生,大家都熟悉,也知道他是一位颇有分歧的人物。表面上大家对他都很客气;偏右的家伙不用说,左派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实际上分歧之大犹如水与火;有原教旨的民主,也有为民作主的’民主’,反正你懂得。相反,关于赛先生,大家没有分歧,无论左派或右派,对他都很敬重;除了某个时期,某些带有不正常脑神经的人是例外,现在谁也不会说要把赛先生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正相反,政府正把大把大把的钱投进科学研究,要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我相信中国(大陆)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迟早的事;至于多迟多早,可能政府已有精密的规划,不是我们平头百姓要操心的事。
但是,我们真的已经把赛先生请进了中国,并安家落户吗?我认为这是一个还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我们知道赛先生所代表的是一种完整的科学体系,包含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二个方面。对大多数国人而言,一提到’科学’我们就会想到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例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或计算机,互联网和航天登月等等;广义来讲,也包括社会科学和一部分人文科学。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所学到一切,包括文科和理科,都是现成的科学知识;但老师很少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学者们如何从现象出发,通过严密的科学思维,得到正确的结论,最后成为我们今天所学的科学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同胞中的绝大多数仅仅学了科学知识,不一定学到了科学的思维方式;而正确的科学的思维方式正是获得科学知识的前提。我们都在反思,近代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出原创性,突破性的新知识;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普遍地缺乏正确的科学思维训练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缺乏一种自由的气氛以有利于鼓励和培养青年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另文论述。)
在科学思维中,最主要的三个要素是:思维的理性化,推论的逻辑化和结论的实证化。
自古希腊以来,理性思维与知识之获得这之间的关系是哲学家们反复思辨的对象。撇开哲学家的深邃理论,对我们平头百姓而言,科学思维包含了二个方面:一个是方法,一个是态度。理性的科学方法就是指要应用合适的现象和事实,以符合逻辑的推理方式,导出相应的结论。理性的态度是指在材料收集,推理过程和作出结论的各个环节中能保持客观,审慎,理智和深思熟虑,更不能感情用事。这些思维上的要求好像都是不證自明的常识。所有受过一些教育的人, 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自己能进行理性的思维。但是仔细观察,我和我周围的人的思维都或多或少会偏离理性化的要求。
譬如,最近一位朋友转来了一篇关于维生素B2的文章,著者是北京大学医学院聂松青教授。我不是医学专家,对此文章我本无缘置啄,但对文章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作一些分析。一开始著者给了我们几个结论:”1、身体长期、严重缺乏维生素B2是导致癌症、肿瘤的根本原因;2 、各种消化道溃疡、出血、肿块、息肉、肌瘤、肝硬化也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所引起的;3、痔疮也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引起的;4、女性的宫颈糜烂也是因为缺乏维生素B2引起的;5、通常所说的”上火”就是维生素B2 短期、急剧缺乏症。” 这里,著者是在叙述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原因是缺乏维生素B2,结果是导致癌症,肿瘤,消化道溃疡,出血,肿块,息肉,肌瘤,肝硬化等等疾病。我相信聂教授在临床上一定见到过有些肿瘤或其他疾病的患者缺乏维生素B2。但我不知道她(或者其他学者)是否做过流行病学研究,并发现了这二者有正相关性。
另外,聂教授不仅说有相关性,还主张有因果性,也就是已经有研究结果能证明长期严重缺乏维生素B2至少会在实验动物上导致癌症的发生。如果聂教授拥有自己或别人的流行病学和科学实验结果,那么她的结论无疑是理性的。但是,当我就此向医生和因特网求证,回答都是否定的,即不存在相关的流行病学或科学实验的研究结果。如果聂教授仅仅根据自己的临床观察而作出这些结论,那么说明她还没有掌握理性的思维方式,因为她收集的资料是零碎化的,推理的逻辑是跳跃式的,结论是缺乏实证的。
专家教授都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如果他们把学到的科学知识来支持他们不科学的’科学’结论,那就会把事情搞得更复杂。譬如上面提到的那位聂教授,她想用她的病理学知识来证明上述结论是有’科学’道理的。聂教授论述道:”当缺乏维生素B2 时,血管壁(主要是毛细血管, 管壁本身就很薄)开始变薄,在血压的作用下,血管开始向外凸起,当局部的血管都开始鼓起时,就形成了肿块,最后血管开始裂开出血,如果发生在脑部……这就是脑溢血……发生在食道,就是食道溃疡;发生在胃里,就是胃溃疡;发生在肠道,就是肠道溃疡;发生在女性的子宫颈,就是宫颈糜烂……充血、肿胀要是长期、持续发展下去,就会凸出组织、器官的表面,形成肿瘤,肿瘤发展到最后阶段,表面糜烂,反复感染、化脓,内部细胞疯狂增生,这就是癌症。 “可惜的是这些貌似’科学’的病理学描述并没有实验数据的支持,更不是医学界的共识,而只是聂教授应用她学到的病理学知识用非理性的思维方式作出的似是而非的推论。但这些带有医学词汇的论述用来镇住普通百姓是足足有余的;因此,如此之类的文章和铺天盖地的养生谬论能在网上广泛传播就不奇怪了。
聂教授可能是一位医学知识很渊博的好医生。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不是同一件事情。学了一些科学知识并不意味着学会了科学思维。另外,有科学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并不意味着他都能在任何情况下应用这种能力。这在科学家中也并不罕见。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对美国科学院院士做过一个调查,在生物学家中不信神和不信永生的比例分别为65%和69%,在物理学家中分别是79%和76%。换句话说,还有一小部分科学家相信神和永生。毫无疑问,这小部分相信神的科学家之所以能作出杰出成就而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就是因为在他的研究领域中有能力进行科学理性的思维。这个现象说明一个人可以在一些领域中具有应用理性思维的能力,而在另外的一些领域中则不能。
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从对客体的观察和感知开始,并形成定义和概念;有了精确的定义和概念才能进行逻辑性的思维和推理。一般而言,自然科学研究对象,譬如上面提到的维生素B2和肿瘤或癌症,定义和概念都是十分清晰。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精确的定义和概念当然也是同样重要的,虽然由于社会现象的繁复性而会带来一些困难。但是, 如果对一个社会研究的对象定义模糊,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岐义。
对一个定义模糊社会现象,就不可能做任何有意义的讨论。最近看到刘军宁先生一篇文章,题为”好的政治秩序需要尊天纪”。此文的中心思想是”……一个好的政治秩序非常依赖于我们对天道的理解并把这个天道转化成制度。在此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一定要承认天道的存在,对它表示很大的尊敬,而且不试图用人的意志去任意的取代它或者任意的界定它……”。我把文章读了三遍,仍未找到著者对’天纪’或’天道’下的定义。
文中最接近’天纪’或’天道’的定义是”……来自于一种超越性的这种来自于造物主的一种秩序的理念,就是持久的、超越的道德原则,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天纪”。但这是一套什么样的”秩序的理念”或”道德原则”,至少就我而言,仍是云里雾里;因此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对它表示很大的尊敬”,为什么要”把这个天道转化成制度”,为什么不能”用人的意志去任意的(地)取代它或者任意的(地)界定它”?由此可见,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对研究对象的定义和概念作出精确的界定;然后才能进一步作出理性的有说服力的推论。
定义和概念被精确地界定之后,诡辩就比较容易被识破。譬如,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生而平等’是一条公理;它是指在一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享有若干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根据这条公理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 譬如,如果选举权是男性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选举权也应该是是女性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根据这条公理我们也可以下结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户籍制是一种不公正的立法。一个人由于出生于农村或城市之不同的而享有不同的教育权,医疗权, 居住权,这明显违反’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因此,’人生而平等’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十分清楚的,它指的是’权利’,而非其它。陈天生先生在光明网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人生而平等吗?”。该文章的核心论点是”(人)从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一个生命,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地区(城市与乡村)、不同的家庭,就有不同的差异,就其生命的个体来说,是男是女,体质好坏、智商高低,也存在着差异。
可以说,这种”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差异,决定了一个人不平等的社会位差和不同的生存方式。” 陈先生在这里很正确地叙述了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可能具有的’状态’的差别。但是,很明显,陈先生在这里使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技巧来讨论’人生而平等’这命题。在’人生而平等’ 这命题里,它所定义的概念是’权利’的平等,而不是指’状态’的平等。陈先生就是想用人生而具有的’状态’的差别,来证明一个人生而具有的’权利’也是有差别的。这种在’权利’和’状态’二个概念上偷梁换柱,既不是严肃的学术辩论,更不可能伤及’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文明社会的共识。陈先生可能就是想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龙生龙,凤生凤’的口号找到一些理论基础。
在应用理性思维的能力上,总的来讲,自然科学家要比社会科学家强一些;这可能和研究对象的差别有关。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独立于研究者之外,而且研究方法大体上也有一个程式,从现象或实验的观察和记录,经过分析,总结,归纳和推断,最后到结论的验证。在这过程中一个人比较容易保持客观和审慎。
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和由人组成的群体的特性和运动规律,因此研究者本身也处在研究对象之中。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群体的关系,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感情,信仰,道德,文化,种族,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因此,要求社会科学家以客观,审慎,理智和深思熟虑态度来进行理性的思维,就成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更何况人是社会动物, 研究者还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安危等问题。
但是,若社会科学家没有客观,审慎,理智和深思熟虑的态度和精神,又如何能求得真理呢?我们平头百姓又如何相信你的观点或研究结果是正确和客观的呢?基于此,我对一星期来我浏览过的政论性文章作了统计,结果是80%以上的文章在科学思维上,至少我认为,都可以找出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因为自身理性思维能力不足;而更多的是观点立场先行,然后罗列一堆理由,即使这些理由在逻辑上并不能支撑他的结论也在所不惜;或者有意模糊定义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来进行文字游戏;还有一些完全是不讲逻辑,不讲理性的强词夺理。无疑,同自然科学家一样,社会科学家需要掌握科学理性思维的方法和态度;而非功利性,非情绪性的态度对社会科学家而言尤为重要。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毫无疑问,钱学森先生是一位大科学家。可是,当钱先生也会去论证’亩产万斤’,去论证’大炼钢铁’,去论证’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环境下,人们如何能进行理性的科学思维呢? 极具科学思维能力的钱先生也不能处处坚持他的科学思维,这又说明了什么呢?缺乏一个自由的科学思维环境和缺乏科学思维能力一样,不可能产生出原创性突破性的科学成果。
因此,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线索就在钱学森先生身上。如果把具有完全的理性科学思维能力定为100分,作为一个整体,以我的观察,美国人可得60分,西欧人可得65分,中国人可得15-20分。因此,当大家都一致同意,而且已经把赛先生的’科学知识’这部分请进来之后,现在把赛先生的另一半,也是更基础更重要的一半,即理性的’科学思维’,真正请进来就变得刻不容缓了。如果把理性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精神融合到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中,那么,过了二代三代之后,我想我们整体的科学思维能力可能会提升到30-40分。到那时候,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人就不是一个二个,而会是一批人。到那时候,从世界看中国,它将是一个显得更有理性的民族。
赛先生,再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