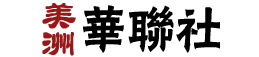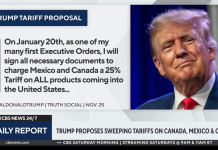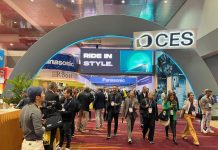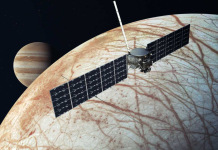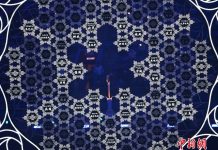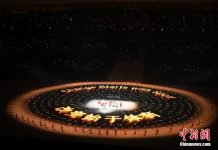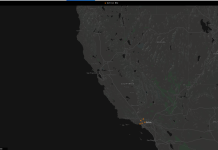【美洲华联社讯】近日,国内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创造出“免疫艾滋病婴儿”的新闻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人们认为这项技术侵犯了人类伦理。美国学者福山也在著作中给出了自己对基因工程的看法,在他眼中,这项技术不仅有损伦理,在技术上也疑难重重。它极有可能颠覆现代政治,将人类带入“后人类时代”。
本文摘编自弗朗西斯·福山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第5章《基因工程》以及第6章《我们为什么应该担忧》。顺序有所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美国学者福山:基因工程将颠覆二十一世纪的政治
宣布基因编辑婴儿诞生的科学家贺建奎
用基因塑造婴儿的可行性
现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诞生人工婴儿。详细说来,科学家将能够辨认出决定一个人特征的基因,比如智商、身高、发色、进攻性或自尊感等,并用这些知识来塑造一个条件更好的婴儿。这个尚在探寻中的基因还可能并不是来自人类本身。
生殖细胞系基因工程已经在农业领域得到例行应用,在很多动物身上也已成功实施。对生殖细胞系基因的修改,理论上,只要改变受精卵内的一组DNA分子,随后通过细胞的分裂和分化,就能长出一个完整的人。体细胞基因疗法只会改变体细胞的DNA,因此也只能对受改造的本人有影响,而生殖细胞系基因的改变则有遗传的作用。这对治疗遗传疾病特别有吸引力,比如糖尿病。
可是,在人类利用这些方式对基因进行改变前,有一大堆棘手的难题摆在眼前。首先就是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早前我们已经知道许多疾病是由于基因间的互动所引起的,而通常一个基因也可能有多种功用。以引起镰状细胞性贫血的等位基因来说,它还具有抵抗疟疾的功能;这也说明为什么黑人特别容易患镰状细胞性贫血症,追溯到非洲祖先,疟疾曾是一个主要的病症。修复镰状细胞性贫血基因可能会增大患疟疾的脆弱性,这对住在北美的人来说也许不是个问题,但是对携带新基因的非洲人却有很大的伤害。
基因常被用来比喻成生态系统,一环扣一环:用爱德华·威尔逊的话来说:“遗传就好比环境,你不能只担心一件事情。当一个基因因为突变或被其他基因取代而改变,一些未曾预期、极有可能非常令人沮丧的副作用也会紧随而来”。
基因工程与优生学的阴影
基因的多重功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极端复杂性并不意味着在完全弄清这些作用模式前,人类基因工程会一筹莫展。从来没有技术以这种方式进行。很多时候,一项新式药品被发明、试用或许可上市时,厂家并不能完全确认它们的疗效。基因工程师可以先解决简单的问题,然后一步步拾级而上,向复杂性出发。虽然看起来人类高端的行为是由于许多基因的复杂互动引起的,但我们并不能知晓是否永远如此。可能某些相对简单的基因干预会产生极大的行为反应,我们却受困于复杂性思维。
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对整个人群产生显著的影响,它必须是非常有用、相当安全和价格低廉的。人工婴儿初期一定会相当昂贵,仅仅成为富人的选择。人工婴儿是否会越来越便宜并因此而流行起来,这取决于科技进展的速度,比如,可以比较胚胎着床前诊断下降的价格曲线。没有人知道,将来基因工程是否会如超声波和堕胎一样便宜和随处可见。这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它所能带来的好处。
当前在生物伦理学家看来最为普遍的担忧是,这一技术只有富人可及。假使,将来的生物技术能够使用一种相当安全且行之有效的基因手段,来制造更为高智商的孩子,那么这一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这种情形下,发达和民主福利的国家将会重新进入优生游戏,这一次不是为了阻止低智商婴儿的出生,而是用基因手段帮助天生残缺的人提升他们及他们后代的智商。这时,国家会要求这种技术的价格保持在低廉和人人可及的水准。这时,一个全人类层面的影响将真正成为可能。
优生学是悬在整个基因学之上的幽灵。以往优生理念的第二个缺陷是它由国家支持且带有强制性。纳粹党把这一政策演绎到令人十分恐惧的极端地步,滥杀无辜,在“劣等人”身上做实验。考虑到酗酒、犯罪倾向等许多行为有可能遗传,这就会让国家在大多数人口生育的问题上有了潜在的支配性权力。
当谈到未来的基因工程时,我个人更偏好放弃使用已经不堪重负的“优生学”一词,取而代之以“选育”(breeding)一词。未来,我们极有可能像育种动物一般选育人类,只是手法更加科学、方式更为有效,我们将通过基因遴选决定哪些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选育已经不必要有“国家力挺”的内涵,更适当的表达是,它显示了基因工程不断“去人类化”的潜质。
据自然科学家马特·里德利观察,国家扶持是过往优生法令的最大弊端;如果由个人自由来决定是否优生,不会产生这类污点。
《我们的后人类未来》,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1月
个人自由选择优生,果真能避开伦理污点吗?
假定新式生物技术的采用,如基因工程,主要出自父母方个人的选择而非国家的强制性命令,是否仍然会对个人或社会整体带来危害呢?
最明显的一类伤害我们耳熟能详,来自传统医学领域:采用生物技术新手段可能带来副作用,以及其后长期治疗过程中会产生负面效应。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或其他管理性机构存在的理由就是要阻止此类伤害的产生,在产品投放市场之前通过现有医疗检测手段反复试验。
根据经济学理论,只有当个人选择导致“负外部性”——也就是说,当危害带来的代价由完全没有参与交易的第三方来承担时——社会危害才会形成集成式影响。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过向当地的河流倾倒有毒废料而获益,但它会影响到附近社区成员的利益。类似的效果已经在Bt转基因玉米上体现出来:它能够制造毒素杀死一种欧洲当地的害虫玉米螟,然而,它也会因此误杀帝王蝶。(后来表明,这项指控是不实的。)这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由生物技术方面的个人选择带来负外部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受累?
在基因更改中,没有被征求是否同意但却是参与主体的孩子,很显然就是可能受到潜在伤害的第三方。现行的家庭法假定父母与孩子间有共同的利益,因而会在抚养和教育后代上给予父母较大空间。自由至上主义者强调,既然大多数父母只想给予孩子最好的,这意味着孩子某种程度的隐性同意,孩子是更高智商、更好看的容貌和更满意的基因特质的直接受益方。然而,仍然存在较多的可能,对于生育技术的选择对父母是有利的,而对孩子则可能带来伤害。
什么符合孩子最好的利益?父母在此问题上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决断,因为他们通常依据自己的议程来征询并依赖科学家与医生的建议。出于单纯野心希望掌控人类本性,或在纯粹意识形态假定的基础上设定人类可以成为的样子,这种冲动实在太司空见惯了。
基因工程在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以人类基因工程可能会产生未曾预料的效果为由,或它可能并不能产生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为由,并不能阻止人们去尝试它。科技发展史上遍布着因为长期副作用而被更改或被遗弃的新发明。比如,过去几十年,发达国家从来没有尝试大规模的水力发电项目,除非产生阶段性的能源危机或迅速增长的用电需求。这是因为,在大坝建设风行期,美国相继在1923年建设了赫奇水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立了田纳西河流管理局;然而环保的意识很快就高涨起来,呼吁考量水力发电的长期环境后果。现在再来回顾建设胡佛大坝时的“英雄”之举和那时拍摄的斯大林式的庆祝影片,对于这一段人类征服自然的“光辉岁月”,以及罔顾生态环境的“轻率”之举有一种离奇的生疏感。
人类基因工程只是通向未来的第四条道路,也许是生物技术发展上最遥不可及的阶段。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改变人性的能力,也许将来也不会拥有这种能力。但这里仍要强调两点。
首先,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为现实,生物技术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对基因因果链的更为熟悉的了解、神经药理学的进展以及寿命的延长——仍然会对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争议,因为它们挑战了人们深为珍视的平等和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这些发展给了社会新的控制公民行为的手段;这些发展会改变我们对人的品性及认同的传统理解;这些发展将会颠倒现存的社会结构,深深改变人们智商、财富的比例以及政治进程;这些发展将会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质。
其次,即便对人类整个种族产生影响的基因工程需要二十五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它却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生物技术的进展。这是因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这些都会因为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得到颠覆性的改变。(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