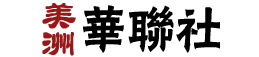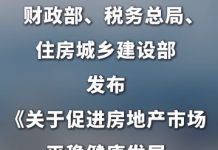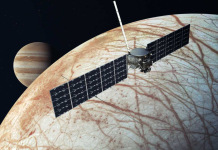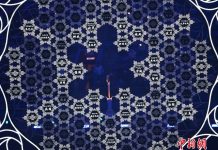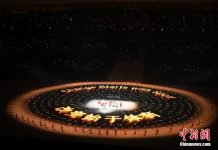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美洲华联社讯】8月底自欧洲开会、旅游后转抵纽约长子润生家。9月1日,在香港中大同事给我的传真中,惊悉钱宾四先生于8月30日谢世了。内子元祯与我相对怃然,太息久之。从1977年以来,钱先生在我夫妇心目中,不只是一位望重士林的国学大师,更是一位言谈亲切、风趣可爱的长者。
钱穆
9月3日,从纽约返港后,即参与中大及钱先生生前在港有关的教育文化机构筹备追悼会的事。校方决定由我与新亚书院院长林聪标教授代表香港中文大学专程到台北参加9月26日钱先生的祭礼。香港各界并定月之30日在马料水中大校园举行隆重之追悼仪式。钱先生一生从事学术与教育,创建新亚也许是他所花心血最多的。钱先生担任新亚创校校长达十五年之久,新亚创校初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时无丝毫经济凭借,由于他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对中国文化理念之坚持,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情形下,以曾文正“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获得雅礼协会、哈佛燕京社等等的尊敬与支持,到1963年新亚与崇基、联合两书院结合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新亚自此得到了一个经济上长远发展的基础,而也就在这个时刻,钱先生决定自新亚引退了。他这种“为而不有”的精神正是他所欣赏的虚云和尚的人生态度。虚云和尚在七十八高龄之后,每每到了一处,筚路蓝缕,创新一寺,但到寺院兴建完成,他却翩然离去。钱先生虽离开新亚,新亚还是与他分不开的。我之有幸与钱先生结识,也纯缘于新亚。
1977年7月,我承接新亚院长之初,曾去台北士林素书楼拜谒宾四先生。在中学时,已读钱先生的《国史大纲》,但从未与先生见过面,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久所仰慕的大学者。虽然初晤,但钱先生温煦和蔼,讲话娓娓动人,令人如坐春风。钱先生不多虚语,却甚健谈。他善于讲,也善于听,始终给人充分空间,不会自说自话。告辞时,钱先生送我,一再说“一见如故”,还说我们有缘。自此之后,我每次返台,只要时间许可,一定去素书楼,一谈就至少二三小时,几乎次次在钱府午膳,常常品尝到钱夫人精致的小菜。在早时钱先生体力尚好,他与夫人有几次还陪我夫妇游阳明山、北投诸景。钱先生喜欢风景,即使眼力不佳,也丝毫没有减少一近山水的兴头。素书楼,有松有竹,园不算大,但自有风致,进门斜坡路上两旁数十棵枫树尤其摇曳多姿。园中一草一木,大都是钱先生与夫人亲自选择或种植的,他与夫人在楼廊闲话时,抬眼就可欣赏到园中的青松。今夏自素书楼搬到市区后,尽管钱夫人把客厅的一桌一椅布置得与往昔一模一样,但新居无楼无廊,更看不到廊外那株枝干峻拔的青松了。
钱先生以九十六高龄仙去,一生在学问与教育事业上有如许的大成就,可以说不虚此生。报载钱先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宾老离开这世界时确是平平静静的。我最后见他的一面是在今年6月“国是会议”后的第二天,那时他刚搬去杭州南路不久。像往时一样,他坐在与素书楼客厅同一位置的同一张红木椅上,面容消瘦,但那天精神比一年前所见似要好些,只是绝少开口了。记得他要了支烟,静静地抽着,听到我与钱夫人提到熟悉的事,他安详地点头,偶尔还绽露一丝笑容。是的,近二三年来,钱先生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享受不到昔日与宾老谈话之乐了。倬云兄去年在见了钱先生后跟我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诚然,宾老不死,只是隐入历史。
宾四先生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他的高足余英时先生以“一生为故国招魂”来诠释这位史学大师的志业宏愿。从结识钱先生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应该说自“五四”以来的学术大气候流行后,钱先生在心灵上已是一位“流亡的文化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他对自己有些著作之传世,极有自信。他曾特别提及《先秦诸子系年》这部书。多年来,他的著作在内地受到批判,但近年,他的书一一在内地重版问世了。这一点,他是感到安慰的。宾四先生的寂寞主要靠书、靠做学问来消解,上友古人,下与来者,自然有大共鸣。有一次我问:“先秦诸子不计,如在国史中可请三位学者来与您欢聚,您请哪三位?”朱子、曾国藩,他略作思索后说,第三位是陶渊明。钱先生的心灵世界是宽阔的,他在古人的友群中,有史学的、理学的、文学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欣赏,他是言之不尽的。记得最后几次谈话中,他强调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这几晚,在深夜,不时展读钱先生先后寄给我的三十余通亲笔函。1977年最先两封是毛笔写的。钱先生的字自成一体,清逸中带凝重,规矩中有洒脱,书趣盎然。不久之后,由于患黄斑变性症眼疾,目力大减,钱先生改用钢笔或原子笔,到了后来,目力又弱,所书常是一字叠在另一字上,而封面则由钱夫人代写。钱先生一生多在读书写书中度过,晚年眼疾,既不能读,又苦于写,一定给他许多痛苦。我知最后几年他写文章全凭记忆,而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则成为他唯一的依靠。为了整理宾四先生的旧稿,胡女士需一字字诵读,钱先生则一边听,一边逐字修改。一遍之后,复又一遍,如是者再,可谓字字辛苦,得来不易,而数百万言的书稿就是这样整理完成的。识者都了解,没有钱夫人,钱先生不可能享此高寿,更不要说他离开新亚之后,还有这么多著作与世人见面了。故我一谈到钱夫人,钱先生的门生没有不油然生尊敬感激之心的,而钱先生在内地的几位子女对钱夫人的由衷敬爱,我是目见的,胡美琦女士是钱先生的真正知己,也是真正在钱先生大寂寞中生大共鸣者。
余英时
十三年来,在与钱先生的交往中,有太多可以怀忆的事。我始终视钱先生为前辈长者,由于我无缘跟他读过书,故他一直以朋友之义待我,与我成为了忘年之交。一次钱先生问内子本姓与祖籍,元祯告以姓陶,祖籍无锡,钱先生笑说:“那我们是一家人呀!在无锡,钱陶是一家,钱陶是不通婚的。”他曾尝过元祯烹调的无锡肉骨头,居然大加夸奖,说是有家乡味。元祯绝少参与我的事,即使我在新亚主办的几个讲座,她也鲜少参与,唯一的例外是钱先生在“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中的六次讲演,总题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她次次都在座,并且听得津津有味。的确,钱先生的演讲是名副其实地又演又讲,并且深入浅出,曲曲传神。他自己讲得投入,听众也投入,无怪乎当年他在北大成为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而有北胡(胡适)南钱之说(当然这不仅仅是指二位的演讲出色而已)。不过,钱先生的口音却只有江浙人才能心领神会,广东籍学生就听上三数个月,也只能“见木不见林”(只能听懂人名地名,但掌握不到整个演讲的内容)的。钱先生倒不觉得他的话不标准,在讲座开讲前,他的新亚老学生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指译为粤语,钱先生似明不明地反问:“需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听不懂中国话呢?”
新亚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每年邀请国际上卓有成就的中外学者演讲,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与内地的朱光潜先生担任讲座时,钱先生特地来港晤聚。前者是彼此相慕已久,东西学术巨子的见面;后者是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的重晤,当时在香港文化界都成为盛事与佳话。新亚有几个讲座与学人访问计划,当我告诉钱先生新亚有意邀请内地学人交流访问的构想时,钱先生是最支持这一想法的。他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学术文化在政治之上之外,香港在内地与台湾的学术文化交流上应该有重要作为,钱先生对学术文化的交流有独特的看法,他说学术思想是“文化财”,文化财的交流是,你有了,我也不会少,彼此都有益,彼此都会富有些。钱先生对于中国文化之存于天地之间的信念,丝毫不怀疑,他对1978年后内地的改革寄以希望。由于客观的政治环境,宾四先生自1949年南来香港后,再未曾踏上内地一步,但他对神州故土之怀念是无时不在的。当我1985年去内地前,钱先生知我要去无锡、苏州,特别高兴,说我一定会欣赏无锡的太湖景色,并且嘱我一游苏州拙政、网师诸名园之外的耦园,耦园是他念念不忘的当年著述游息之处。宾四先生对于故里的情怀,溢于言表。
灯下,写此短文时,宾四先生生前种种情景,一一重来眼前,他在我夫妇心目中,一直是一位言谈亲切、风趣可爱的长者。现在长者已去,他已隐入历史之中,后之来者,只有在历史中寻觅他的声音容貌了!
1990年9月14日深夜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本文摘自《有缘有幸同斯世》,金耀基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