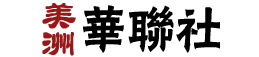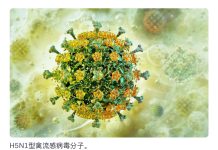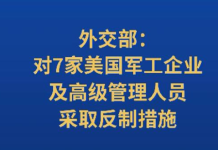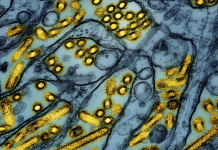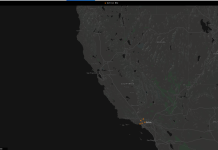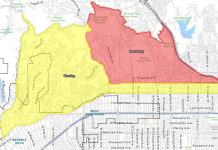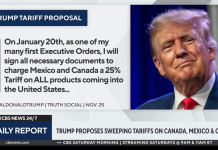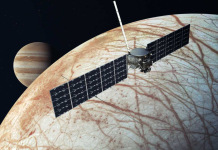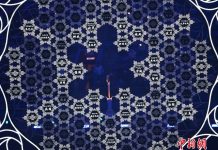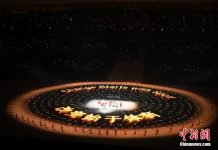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美洲华联社讯】1949年春夏,上海,空气里弥漫着紧张,行路的人总是神色匆匆。共产党步步逼近,国民党节节败退。面对即将来临的红色革命,上海的商人、地主、买办和知识分子都在悄声低语:要走吗?还是留下来?可以去哪?
1982年,华裔美国人陈果仁因为看上去像日本人被两名白人汽车工杀害。十年后,谢汉兰继续为受害者家庭发声,并呼吁人们关注更大的种族暴力问题。 COURTESY OF HELEN ZIA
华裔作家谢汉兰(Helen Zia)的英文新书《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逃离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人的史诗故事》(The Last Boat Out of Shanghai: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ese Who Fled Mao’s Revolution)讲述的便是这一时代背景下,四名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少男少女从上海出逃的周折经历。中国战争史上这一篇章与谢汉兰息息相关——书中的一位女主角正是她的妈妈。
谢汉兰的母亲在战乱中被多番抛弃,先是被苏州一户人家领养,后来跟着“新妈妈”逃到上海,又被转手送给另一户上海人家,直到1949年解放军即将占领上海之际,才最终逃往美国。然而,关于这些过往,她的妈妈几乎只字不提,直到晚年,才将一切和盘托出。谢汉兰近期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道:
“第一次听到母亲的故事,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难民和移民选择不告诉子女自己当年离开上海的故事。他们已经找到了避难所,可以全力鼓励孩子们充分发挥潜力,得到他们自己没有得到的机会,为什么还要回忆那些创伤和苦难呢?”
作为上海难民的后代,谢汉兰的人生经历与她母亲的很不同。她出生在美国新泽西的一个小镇,那里的东方面孔并不多。谢汉兰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个男女混合的班级,但在念研究生期间,她毅然从医学院辍学,跑去当了建筑工人,后来又进入汽车工厂,成为工会活跃分子。同一时间,她开始为本地和全国性刊物供稿,此后历任《旅游周刊》(Travel Weekly)主编、《女士杂志》(Ms. Magazine)执行编辑等职位。
1992年,当谢汉兰离开美国著名女权主义出版物《女士》杂志时,她的同事们以她为主角仿制了一期封面。 COURTESY OF HELEN ZIA
民权运动和亚裔美国人的生存环境一直是谢汉兰最为关注的几个议题。她曾参与创办美国公民正义会(American Citizens for Justice),将1982年美国仇日情绪大爆发中被误杀的华裔陈果仁(Vincent Chin)的案件推向大众视野, 并在2000年出版的《亚裔美国梦》(Asian American Dreams)一书中详细回顾了这一里程碑事件。她还作为执笔人撰写了1999年被美国政府错误指控为“中国间谍”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Wen Ho Lee)的自传。
2007年,谢汉兰获得富布莱特奖,启动了上海移民潮的研究。为完成《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她展开了长达12年的调查与走访。期间,她在上海生活了5个月。
近日,谢汉兰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访谈,采访以英文、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内容经过编辑与删剪。
1950年,谢汉兰的母亲(左一)在曼哈顿华埠宰也街和披露街的古玩店工作。 ZIA FAMILY
纽约时报中文网:生活在和平与繁荣的现代中国,为什么了解上海移民潮这段动荡历史对中国年轻人来说仍然意义重大?现在越来越多担心经济不确定性的中国商界精英再次选择离开中国,或者至少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国外,他们能从中学到什么教训?
谢汉兰:历史上,真实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从来都不那么美好或简单。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巨大动荡时期,人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这本书讲述了上海人的故事和他们做出的选择,而没有判断这些选择是对是错。对其他人来说,问问自己:“如果我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试着决定是逃走还是留下,我会怎么做?”这句话很有用,也很重要。
(如今)对那些选择移民的精英来说,考虑将家人送去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资源。但我的书中的一个教训是,普遍来说,任何地位的外国人都会是不受欢迎的,不管他们有多精英、多富有,尤其是在当今全球的紧张和民族主义气氛中,他们注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消极情绪。
1950年代,中国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宋子文(T.V. Soong)曾试图在纽约第五大道最高档的街区买一套公寓,他一度被拒绝,因为其他富裕的白人居民担心,他会在屋内开一家中国洗衣店。我写的关于上海移民潮的书可以提供许多洞见,让我们了解70年前和今天的人们是如何被对待的。如果我能给出一条建议的话,那就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可能去的社会,包括那里的中国人在历史上是如何被对待的。如果人们愿意从历史中学习,他们也许能够避免重复历史。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在书中写道,创作初期,你遇到了一些人不冷不热的反应,他们认为这个话题要么太有争议,要么太过普通。你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为什么用了12年之久才完成了这本书?
谢汉兰:有些人,例如在香港的人,觉得解放时期来到香港的人太多了,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没有特别到值得用一本书来讲述它。另一些人则认为,一本讲述中国解放时期的书可能会引发敏感或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因为这些故事反映的是真实个体的背景和经历,并没有宣称这是所有上海人或中国人的经历。
因为这是中国史和世界史上一个非常重要和动荡的时期,我需要时间来确保我准确地描述了这些历史事件。此外,我还需要找人采访,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由于没有那次移民潮的记录或名单,我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来锁定这些人,并查阅当时的历史档案材料。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提到许多著名的美籍华人曾是上海移民潮的一部分。他们相对富有、受教育程度较高,进一步造就了美国“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这种概括性评价是如何导致对上海人和亚裔美国人的误解的?
谢汉兰:今天,许多美国人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富有,因为当下的中国富人和高干子弟来到美国,他们购买最昂贵的地产、豪华汽车、奢侈手表和名牌服装等。与今天不同的是,70年前,那些作为移民潮一部分来到美国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富裕。他们大多是研究生和专业人才。当然,也有一些非常富有的人,比如宋美龄和她的家人,但大多数都不是。
然而,许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不希望与中国餐馆和洗衣店的工人混在一起——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唯一被允许在美国从事的工作。相反地,像大多数其他美国人一样(包括白人),在这场可怕的世界大战之后,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华裔美国人只想在郊区过一种平静安宁的生活。但在20世纪60年代,当非裔美国人领导的民权运动开始呼吁平权并在美国社会中反对种族主义时,这些中产阶级的亚裔美国人被拿来与非裔美国人进行比较,并被打上“模范少数族裔”或“好”少数族群的标签,这当然意味着非裔美国人是“坏”的少数民族。
这种“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并不是亚裔美国人创造的,然而,它的影响却在许多方面伤害了华裔和亚裔美国人。首先,任何使用相同或简单的描述给整个群体贴上标签的刻板印象必定是错误的。其次,这个标签使得美国华人很难得到他们可能需要的任何支持,例如帮助老人和穷人、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语言和教育支援、解决医疗与心理健康问题等。第三,这个标签明显地把华裔、亚裔美国人与非裔、拉美裔美国人对立起来,在这些社区之间造成了巨大的摩擦,甚至引发了暴力。
因此,“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有许多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后果。今天来自中国的访问者、游客和学生需要意识到这种紧张关系的存在并理解其根源,因为他们可能会遇到负面态度而不知道为什么,或不懂得如何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缓解紧张和减少刻板印象。
谢汉兰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72年,她在那里买了一件制服。当她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时,她骄傲地穿着来自中国的衣服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COURTESY OF HELEN ZIA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汽车工业和制造业崩溃,许多人都将此归咎于日本进口汽车。1980年,谢汉兰站在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总部外。那里的标语表明了他们对日本的敌意。 COURTESY OF HELEN ZIA
纽约时报中文网:从医学生到建筑工人、民权活动家,再到编辑和作家,作为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你的经历非比寻常。你为何做出了这些人生决定?你家人的反应是什么?
谢汉兰:事实上,我的经历在当时的美国年轻人中并不罕见,因为那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时期。事实上,这是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青年运动时期,那些希望在世界上产生积极影响的理想主义年轻人领导了这一时代。我认识许多华裔美国人和我这一代的其他美国人,他们希望像中国领导人所劝说的那样,“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我也一样,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我从医学院退学,并成为一名社区组织者的原因。
当然,我的父母并不高兴,因为每个移民家庭的梦想都是让一个孩子成为一名医生——我认为这是因为医生被视为一种高薪、高地位的职业,尽管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职业可供年轻人选择。但那时我已经能自己养活自己,并不依赖父母的支持,虽然让父母不开心我感到很难过,但我必须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梦想和价值观去生活,而不是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当我开始以建筑工人和汽车厂工人的身份挣钱时——我的薪水比一个年轻的医生要更多,我还可以寄钱给我的父母来帮助家庭摆脱困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父母很高兴也很满意地看到,我能够发展一个良好的事业,它还帮助了其他人,促进了华裔美国人社区的进步。虽然他们如今都已不在了,但我知道,他们会为我的新书《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感到非常骄傲,因为它讲述了他们这一代中国人的故事,赞颂了他们在中国乃至世界最动荡、最困难时期的坚强。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妈妈回来看过新上海吗?她对上海的变化有什么看法?她过去住的那栋旧房子怎么样了?
谢汉兰:2006年,我和姐姐带着我妈妈以及她的两个孙女回到了中国。我妈妈一直想去北京——这个国家的首都看看,还有长城。但她对要去上海感到紧张,当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时,她在那里度过了极为艰难的日子。她对上海的变化感到惊讶,但也有复杂的感受,因为她没怎么把上海从她60年前所熟悉的那个城市中认出来,也因为她对日据时期的上海拥有太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们没有找到她曾经住过的地方(那些弄堂和公寓楼),因为它们已经消失了,新的建筑拔地而起、取而代之。
2006年,谢汉兰与母亲在上海南京东路的步行街。这是她的母亲自1949年离开后第一次回到这座城市。 COURTESY OF HELEN ZIA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曾经研究过陈果仁和李文和的案件。从那以后,华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吗?你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引发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和两国之间的各种间谍指控?特别是这些指控对今天在美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如何被认知和对待已经造成了影响。
谢汉兰:我一直说,当美中关系感冒时,在美国的中国人就会得肺炎。陈果仁之所以被杀,就是因为在美日贸易紧张的时期,他“看上去像个日本人”。李文和被诬陷为中国间谍,则是出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反华政治。
不幸的是,美中关系目前的紧张局势和民族主义正在美国引发对中国人的又一轮猜疑高潮。我认为,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和亚洲人都需要保持警醒,并参与到社会中来,以确保政治紧张不会导致对任何群体有害的对待和看法,包括对华裔和亚裔的态度和认知。
陈果仁事件后,谢汉兰和许多人一起加入抗议队伍,反对针对亚洲人和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仇恨。 COURTESY OF HELEN ZIA
纽约时报中文网:你的书中包括许多强势的女性角色,以及她们与男权社会做斗争的故事。在中国刚起步的“#我也是”运动中,年轻女性遇到了很大程度上仍是父权和专制主义社会的阻力,你对她们有什么建议?
谢汉兰:当然,我的观点来自于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的经历,但我是在一个非常男权和传统的中国家庭中长大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很害羞,也很安静,但是我可以看到,相比我的兄弟和父亲,就因为是女性,我和我的母亲是如何被区别对待的。从我最早的记忆中,我就知道这种性别歧视是错误的,也知道我想要接受教育,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用担心因为我是女性,或者因为我并不关心如何才能看起来像一个时装模特,而受到骚扰或歧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会了在我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大声疾呼,也在那些同样认为女性应该能够平等地生活和成长、而不必害怕性骚扰或暴力的男男女女中找到了朋友。找到支持你的同伴,并分享你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做出改变可能并不容易的时候。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一个对女性员工不友好的公司环境中工作,当我了解到我的工资远低于一个工作和责任都比我少得多的男人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当时没有采取公开行动,但我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我最终也找到了改变现状的方法。
我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的经历与中国的情况有任何关联,但今天全球都有了一种性别平等的意识。永远不要忘记,把妇女和女孩当作完整和平等的人来对待,是一个将使全人类变得更好的目标。(文章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