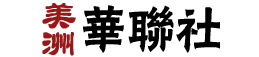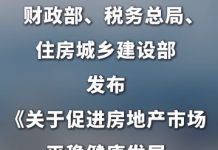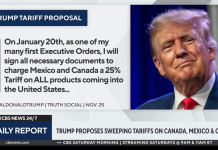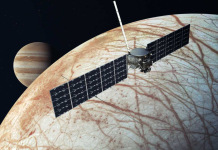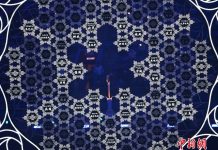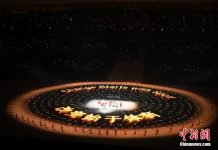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美洲华联社11月11日讯】【宝树按】大约两个月前,有朋友告诉我,北京大学教授吴飞写了一部《三体》的哲学解读,顿时大感“打破次元壁”的惊讶。诚然近四五年间,《三体》已成显学,影响远远超出了狭义的科幻界,科技、文学、未来学、商战等方面的解读已经有不少。不过哲学探讨形而上之道,往往超名绝相,玄而又玄,如何能与具体而微的小说结合?国外偶有此类书籍,也是借一些小说的设定(如“黑客帝国是否存在”“机器人是否应当拥有人权”),普及若干哲学入门知识,与小说本身的关系相当肤浅。
作者的身份是令我讶异的另一个原因。吴飞教授与我算是素识。2005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入北大哲学系执教,其时我在系里读研,虽未选过吴老师的课,但也有幸结识,略有师生之谊。记得硕士论文中有一章节分析柏拉图的《斐多》,正好当时吴老师发表了相关的长篇论文,是我重要的参考资料,受益匪浅,相关问题也曾向吴老师当面请教过。我毕业后远赴海外留学,后来“不务正业”,干脆写起了科幻小说,但对吴老师的学术轨迹,也有所关注。十余年间,他研究过艰深的奥古斯丁的神学,母系氏族的人类学理论,近年更是转向中国传统礼学,如整理出版了清人张锡恭的巨著《丧服郑氏学》,其精力的旺盛与涉猎的多面,在学术界也属罕见。不过无论如何,他能对《三体》有学术关注,是超出我想象的。我也想到,这种解读必然带着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和深入思考,而与上述的“蹭热度”式的写法不同。
正当我感到好奇时,澎湃新闻和三联书店联系我,托我就此书对吴飞教授做一次访谈——大概是知道我曾是吴老师的学生如今又忝列科幻作家之故。我却不敢贸然答应,一是怕这部著作过于高深,访谈也不得其门;二是怕见解相去太远,也难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于是先索书一观。结果证明这些担心完全多余。这本《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虽然只是薄薄一本小书,但承载了作者多年来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紧扣生命意义的问题,依托小说的故事脉络分析和展开,而又不以佶屈聱牙的理论术语吓唬读者,举重若轻,耐人咀嚼。不同背景的读者,只要愿意一同思考,都能有所体会。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模糊疑惑处,令我读后很想更加了解背后的理据,所以我欣然应允了这次访谈,与吴飞老师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对话。
《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
宝树:吴飞老师,您好!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一个中国哲学的会议上,最近知道您出了一本《三体》三部曲的解读《生命的深度》,还是有点吃惊的。虽说很多哲学家都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不过一般公众理解的哲学教授还是在书斋里引经据典,写高深莫测的理论文章的那种形象。如果说会讨论文艺作品,一般也是比较“高雅”的阳春白雪,比如尼采评瓦格纳,或者海德格尔解读荷尔德林这种,那么您怎么会对三体这样一本通俗流行的科幻小说感兴趣,愿意写一本书呢?不光是您,从您的自序中,我看到是赵汀阳老师跟您和杨立华老师约稿,在《哲学动态》上组专题发表,一部科幻小说引起哲学界的如此重视还是非常少见的。所以首先想请您谈一谈写这本书的由来,虽然自序中已经讲到一些,但我想大家会比较感兴趣《三体》和哲学界的奇妙缘分。
吴飞:谢谢宝树。我在《生命的深度》的自序里已经提到,就《三体》写一本书,也是不在我的计划当中的,完全是一个相当偶然的结果,我最开始只是想完成一篇论文。我个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有些触动我的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我也偶尔会写一些评论。我的文集《尘世的惶恐与安慰》《现代生活的古代资源》里都收入了这样的一些文章。不过这些都不是为评论而评论,而往往和我正在关心的学术问题相关。近些年因为独立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少,这种阅读和写作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在做这种评论的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区分究竟是通俗读物还是严肃著作,重要的是其中涉及的问题重要不重要,是否能触动我。《三体》中讨论的问题让很多哲学家有兴趣,除了你提到的杨立华和赵汀阳二位,还有很多人从中受到思想的启发,认为其中触及到了非常根本的哲学问题。
宝树:不过我有个疑问。我跟一些朋友聊过您解读《三体》的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很诧异:小说是虚构的故事,从中怎么能够读出哲学来呢?虽然说法比较粗糙,但其实也反映了自古以来的“诗和哲学”之争。我最近跟大刘也提过您的新作,大刘说还没有读过,但感到十分惶恐,因为恐怕自己的思想太简单,没有什么好解读的。当然,这肯定是过谦了,不过想知道您有没有考虑过从文学中解读哲学思想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作为科幻小说,本身是高度幻想性的,比如说宇宙社会学,黑暗森林法则这些东西,不能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宇宙法则,也不是作者论证的某种理论观点,而是小说的设定。那么您解读出的哲理与小说本身的虚构性质,这二者的潜在矛盾如何处理呢?
吴飞:当然,我也没有把这当成客观存在的宇宙法则。故事是虚构的,并不意味着道理是虚构的。霍布斯讲自然状态,达尔文讲物种起源,何尝不是在讲故事?历史上有过的各种科学范式,不能保证一定是对的,但都包含着重要的哲学问题,可以开启非常深入的思考,甚至会深刻改变我们生活的现实。好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可以读出哲学道理来,这已经不是很新鲜的事了。科幻小说中,不仅包含着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宇宙的可能理解,更包含了对人类与世界命运,乃至生命本质的理解。我自己对科幻小说并不熟悉,而且觉得《三体》与西方多数科幻作品都非常不同。作者建构的一个宏大的宇宙叙事,触及到生命、宇宙、战争、人性等许多永恒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也不会随着宇宙观念的改变而有根本改变,只是提问方式会有不同。因此,《三体》只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把我们带回到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思考。
宝树:这点我同意,小说虽然并非写实,但仍然取材于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和感知,用叙事而非概念辨析的形式表达出来,但其中仍然有自己的思考。甚至于通过不同理念的人的行动和冲突,潜在地有类似柏拉图对话那样的论辩结构……不过有点我觉得您可能评价不太公允,西方的优秀科幻小说也以它们的方式触及到了根本问题,这里既有不同的文化影响,比如西方科幻中宗教性、超越性的主题非常多,中国人可能对这个就不太感兴趣,但也有一些共通的经验和逻辑。
吴飞: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对科幻文学没有专门的研究,所以一些说法并没有深入思考。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西方科幻文学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而是以非常西方式的角度触及这些问题的,所以总能让人联想到希腊神话或基督教。一个文明总有自己的一些思维定式,如果西方作品里面不能找到基督教或希腊文化的元素,我反而觉得不够深刻,无法达到超越性。相对而言,中国作品中如何渗入中国的思维方式,却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太隔膜了。不仅是科幻作品,包括其他门类的文学或影视作品,哪怕讲中国古代的故事,总是用一些非常不中国的方式来诠释。在这个意义上,《三体》是非常独特的,不仅在科幻界而已。我认为,《三体》以及刘慈欣的很多其他小说,虽然设置的场景是科幻,但其中触及的都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如何以中国人的方式思考科幻小说中的大问题,应该就是这本小说最大的特点吧。
宝树:说到中国古代的故事,我想起之前看某版《大闹天宫》电影,套用了非常西式的神族和魔族斗争的框架,很多本来的精髓都丢掉了,让观众看了觉得十分膈应,评价也非常差。还有一些名导拍的古代宫廷武侠大片,画面很美,但中国感也似是而非……这方面,什么文艺都任重道远。在科幻界,近年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科幻是否以及如何具有“中国性”。很多人加入一些诸如方言、中国菜等中国元素,还有人从神话、历史中找灵感,虽然说各有收获,但总体突破不大。但有趣的是,恰恰是《三体》这部似乎并不特别追求中国化的作品,也许反映出中国人某种深层、根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特别是翻译出去之后,外国读者的评论更让我们看到这种不同。关于什么是“中国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点。
吴飞:是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不仅仅是科幻界的问题,而涉及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中国文化认知上面。不是增加一些方言、中国菜,穿一下汉服什么的,就是中国的,关键是中国思考的深度思路。也不见得讲科幻、讲外星人、讲人工智能就一定不是中国的。一谈中国的,我们不能轻易就当做民族主义的,狭义的民族主义,是非常不中国的东西。
宝树:那么回到《三体》,这种若隐若现的中国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本来也没有太思考过这个问题,您在本书中,对生命(zoe)和生活(bios)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和讨论,应该是您的书中最核心的论证之一,对我很有启发。我感觉,在西方哲学中,很容易将生命作为一种物质性质的存在而将生活作为精神或者意义的存在,从而导致一种二分的割裂。所以西方观念中,最美好的生活总是脱离了物质的,在理念或者神那里的生活。但是世俗化以来,对于后者发生了怀疑,所以美好生活本身成为问题。然而这个矛盾或多或少在西方思想中是存在的。比如说作为许多争议焦点的堕胎问题,就是无法处理生活和生命的关系的一种表现。
吴飞:是的。生命与生活的关系就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三体》对我的最大启发,就是帮我重新找回了这个问题。因为近些年我一直在思考“性命”(生命)的问题,所以《三体》帮助我想了很多。就像你说的,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都从“存在”出发来理解生命(生活),所以会有对生活与生命的这种理解,美好生活被当成一种高于纯粹生命的存在,这就是一切问题的所在。我坚持认为,存在不是中国哲学的第一概念,性命(生命)才是。哈姆雷特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其实问的就是“活还是不活”,可一定把它表达为“to be”才有力量,但中文不能译为“存在还是不存在”,这就是哲学思考方式的区别所在。
宝树:《三体》这本书里,没有这种潜在的二元论,生命和生活的关系就变得不一样了。我看到一些外国读者的评论,注意到这本书来自于一种彻底无神论思想,所以其中的意义建构也都是在无神论基础上的——这是中国读者很容易忽略的一点。当然,小说是以故事的形式展现这些思考的。但您的解读则从理性论证上,试图重新梳理生命和生活二者的关系,比如这句话“表层的生命维持与深层的美好生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层面,二者本来就是二而一的整体”(142),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思考。二者的关系在哪里呢?您借用小说的设定,认为生活是在生命基础上的高维展开(30),很有见地。
不过,阅读中我也有一些疑惑,文明的繁盛真的可以和生活的高维展开、生活自身的美好划等号么?小说中地球的命运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我们也可以想象三体人的入侵没有发生,程心和她的支持者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一直存在,而维德等彻底失败(这其实是更接近现实世界的)。但我们仍然感到,程心所代表的价值观不是高维的而是低维的,不是深刻的而是肤浅的,固然其生活可以说是美好,但仍然浮在生活的表层,更接近于尼采讲的“末人”,因此即便没有悲剧的后果,仍然是不可取的。那么,是否美好的生活不能离开生命中一些最原始野蛮的力量的参与呢?美好的生活,它和生命是什么关系?和苦难是什么关系?希望您再展开讲解一下。
吴飞:西方作者的许多科幻作品,不论有意无意,大多能被还原为希腊神话或基督教的某个故事模式,或是英雄传奇,或是牺牲与拯救,或是天使与魔鬼之争,等等。但《三体》不是这样的,它没有那种宗教式的故事模式。杨立华老师的文章里,倒是发现了一种类似《春秋》笔法的写作方式。正是因为脱胎于不同的文化母体,我们从中读到的是非常不同的故事模式。单纯生命和美好生活的区分,其实只是一种设定,在西方存在论的语境下有意义,在中国性命论的语境下没有意义。
《三体》的故事虽然借助于存在论的区分分别触及到了生命的表层与深层,但恰恰表明,这两者是不可区分的。所谓低维与高维展开,也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所以有些地方也说低维展开,但更重要的是,生活的美好与意义就在生命当中,所谓“天命之谓性”、“莫非命也,顺受其正”、“生之谓性”,等说法,都包含着这层意思。这在《生命的深度》第二、三章讲得比较清楚。《三体》第一部中生命与生命的善恶之间并无绝对的区分,如若因为某些人的“恶”而毁灭人类,就会是非常愚蠢的做法。第二部中揭示的黑暗森林理论,虽借助霍布斯、达尔文的区分,其实恰恰消除了西方存在论中生命与生活的高低之分。因而,就第三部而言,程心与维德的区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低维与高维之分,而是生命中两方面的力量:爱与力,即仁与义,柔与刚,阴与阳。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不过书中我这部分没有处理很好,写得并不清楚。
宝树:您这么说我就有点明白了,这种两方面相反相成的方式,避免了一种割裂的二元论。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您在研究中国哲学中提出的“文质论”?生命的基本需求代表“质”的一面,而生活代表文的一面?这和西方人讲的形式与质料不同,文不是外来的、超越的,而是质料内部生发出来的。用科学的语言来讲,相当于一种生命的自组织?可以这么看么?
吴飞:有些关系。不过这两年我已经用“性命论”取代了前几年讲的“文质论”,这本书就是性命论的一个尝试。生物性的生命概念,和文化性的生活善恶,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内在于我们对性命、善恶等问题的理解。这是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我认为这种理解可以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各种著作中找到,但现代人大多很隔膜。《三体》可以帮助我们找回这种感觉。
宝树:那么我可能要提一个尖锐的问题。您在书的最后,用“生生不息”来概括宇宙的命运,体现出中国哲学的精义,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最伟大的能力就是创生生命,近现代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等,就是以此来对抗西方思想中的神。“生命本身的尊严和不朽”,最后也是指向“生生不息的力量和永不放弃的爱”(167),所以生命就是生命自己的基础和意义。不过我感觉,这是否过于理想化了呢?因为小说中,人类文明仍然能够在银河系延续只是非常偶然的结果,是水滴之战后一艘飞船逃出去的结果,而很有可能没逃出去,人类就直接灭绝了。包括现实中,地球生命能够延续数十亿年,也是一种偶然。可能明天一颗小行星砸下来地球所有生命就灭绝了。当然,宇宙别的角落还会创生生命,但那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似乎还是一个神义论的问题:在没有神的世界里,什么都是可能的。而生命是脆弱没有保证的。这个问题在您的著作中似乎处理得比较含糊,想听您进一步解说一下。
吴飞:小说第三部是非常精彩的,我觉得里面有很多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拙作写到最后有些力不从心了,许多问题后来自己才想清楚。中国思想中讲“生生”,从来都是非常具体的生生,即真实的个体生命的生生。至于超越于生命的层面,都是比喻意义上的。个体生命,有生必有死,死生相继,因而生生不息,不能在这个层面上希求不朽,因为没有哪个生命会永远活着,所以理学家说,从枯槁中体会生意,因为死恰恰表明了生。但在更高的层面,比如家族、朝代、国家,以及个人的名声等等,却不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古人讲三不朽,指的从来不是一个人会永远活下去,个体必然会死,但人类集体创造的文明却可能长期延续甚至不朽。顾亭林所讲的“亡国”与“亡天下”,也是在文化意义上讲的。个体的生死相继与人类集体文明的不朽,需要仔细体会。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文明非常不一样。从柏拉图的《斐多》到基督教,“不朽”的最初含义就是个体的永远存在,理念、上帝、灵魂之不朽皆当从此处理解。而《三体》中呈现出的生生与不朽,都要从中国的意义上来理解。个体之生必然有死,哪怕通过冬眠活上几百几千年。但人类文明却有可能不朽,正因为它不是具体意义上的生命。《三体》呈现的正是这样的结局。个体都会死,但人类文明无论通过漂流瓶、宇宙归零,还是什么,却有可能不朽。即便这些都失败了,仍不妨碍生命的生生不息,虽然这种生生不息与地球人已经没关系了。中国的生生哲学充满了温情,但也是非常现实和冷酷的,而这冷酷中仍然透露出生命的力量。
宝树:但我觉得中国古典思想与刘慈欣的、基于当代科学的世界观是不是有一个差别,前者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循环,生命存在的意义是有保证的。而后者是广袤得超乎想象的宇宙,生命在其中渺小可怜。在前者的观念中,人在天地间有属于自身的位置,只要找到这个位置就能“与天地参”。在后者那里,生命——无论是人还是外星人——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必须为种族的生存而战,而追求的也是通过科技的力量不断强大自己,最后掌控宇宙规律,达到不朽。而这与传统中国思想似乎有很大差异。中国思想并不特别追求强大,但黑暗森林的宇宙中必须要无比强大才能生存。生生的哲学如何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呢?
吴飞:当然,古人的天地观与现代的宇宙观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不过,如果你对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也和现代宇宙观非常不同。亚里士多德到托勒密的宇宙观,被李约瑟概括为水晶球式的宇宙模型,在《神曲·天堂篇》里面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反过来再看中国的天地观,我们都很容易想到“杞人忧天”的故事,杞人忧天为什么可笑?因为天不是实体,不可能掉下来,但如果把天地理解为实体,那就会有杞人忧天的担忧。相比而言,现代人似乎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杞人。不过,我想说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有过浑天说、盖天说、宣夜说等种种宇宙理论,人与天地参的意思并不依赖于其中任何一种宇宙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里面说,天圆地方,不是用尺子量出来的方和圆,不必计算尺寸,而是天之道圆,地之道方。人与天地参,也并不是用尺子量出来一个最中间的位置,而是找到一种哲学上的中位。这种哲学上的理解,仍然是可以用来理解现代宇宙的。中国思想是否追求强大,是另外一个复杂问题。我只能说,中国政治哲学不以国家强大为最终目标,但绝不排斥强大,《三体》中不断引述的《三国演义》,就包含了生生哲学不断为求生存和强大提供的智慧。和西方的存在哲学一样,生生哲学不是一种教条,更非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有着丰富的诠释可能性。面对新的宇宙格局,无论对天地人三才的理解,还是对生存与强大的理解,都可以发展出其可能的理解方式,这也正是生生哲学的生命力所在。
宝树:好的,对这些问题,再探讨可能就要进入一些专门概念了,回头我再进一步向您请教。下面我想帮师弟师妹们问一下学哲学的问题。您说“刘慈欣在生活经验和文学写作中对这些重大哲学命题的探讨,远远超过学院中的许多哲学工作者”(27),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许多分析来分析去的哲学命题,除了哲学教授(往往还必须是专门某个领域的)没有谁会感兴趣,对实事本身的思考热情如果最初还有的话,往往也在概念辨析和文字游戏中丧失殆尽。不过您和少数哲学人,仍然是能出入于经典哲学文本和对现实的关注的,所以想请您聊一下,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哲学?怎样让我们的思想贴近于现实世界的关切?
吴飞:哲学这样的学科,完全可能是无用之学。用《三体》中的语言讲,哲学属于生命的高维文明,但高维文明常常成为不着边际的无用之事。现在各大学哲学系中的大部分人和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将来都会被淘汰的。要使哲学成为有用之学,最重要的还是使哲学和生活发生关系。日常生活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是简单的低维展开,其实里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价值和意味,当然也有着非常危险的激流、险滩和礁石,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陷进去。能够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的更多维度,并使我们逐渐学会面对这些问题,学会解释日常生活,做到“极高明而道中庸”,或许是不那么无用的哲学吧。《三体》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帮助我们看到日常生活(而且是非常中国式的日常生活)的这些丰富面向。
宝树:非常赞同您这部分观点,现实人生和日常生活本来就是哲学的持久源泉,很多东西都非常值得思考,但现实中哲学家太多沉浸于抽象命题,这方面往往被宗教和心灵鸡汤占领,是很可惜的。我们希望哲学能有一个整体的转向。最后问个我个人比较想了解的问题,前面聊过,您的学术兴趣很广泛,从人类学到西方古典哲学,再到中国的礼学,现在又讨论到当代科幻小说,但又似乎“道一以贯之”,一直围绕着“生命的意义”这个点。想知道您的下一步研究目标是什么?是在这些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和挖掘呢?还是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有没有计划过写一部独立系统阐释自己思考的著作?
吴飞:这些年我已经把自己的研究收束到对性命论哲学的阐释上面,主要依托于经学文献,同时参照诸子著述,在与西方存在论的对比中,将经学中的性命论体系阐释出来。最近两个月,我在认真阅读丁耘老师的《道体学引论》,读出来我们更多的相通之处,也看到了性命论与道体学两种思路的差别。说是收束到一个问题上,但为此做的准备和读的书很多,写作也非常艰难。不过我相信中国智慧的力量,也相信六经是中国智慧最高的表现形态,其中有一个非常强大、非常系统,也有丰富的解释空间的思想体系。郑玄与朱子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诠释了这个体系,成为汉宋之学的两大高峰。现代人要讲出中国思想的意义,必须以现代方式重新阐释这一体系,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在这方面做一尝试,集中于“性命”的问题。至于科幻小说,并不是我的一个研究领域,这只是客串一下而已,目的是为了打开性命哲学的思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阅读《三体》还是写这本小书,对我确实帮助很大,为此必须感谢刘慈欣先生。
宝树:好的,非常期待您的下一部著作。我也相信有很多《三体》的读者会感谢您解读的启发,虽然可能不少人对您的学术路径比较陌生,也不一定都同意您的观点。不过我曾经在其他地方提过,科幻作品具有一种“边缘”的特点,对于科学、文学、社会等各方面都是边缘的,古怪的,似是而非的,但这种边缘又恰恰是各种艺术和思想的交汇之处。科幻让人们得以和一些完全陌生的观念相遇和对话,碰撞出更多火花。哲学家为《三体》倾倒,当作如是观,而对于《三体》的许多粉丝来说,在此与一种来自古典中国的哲学思考相遇,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相遇,也许就是生命最美好的一种“高维展开”吧。(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