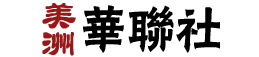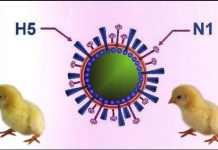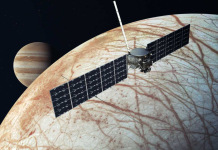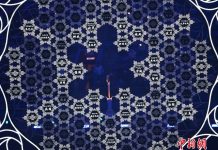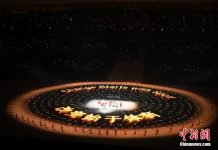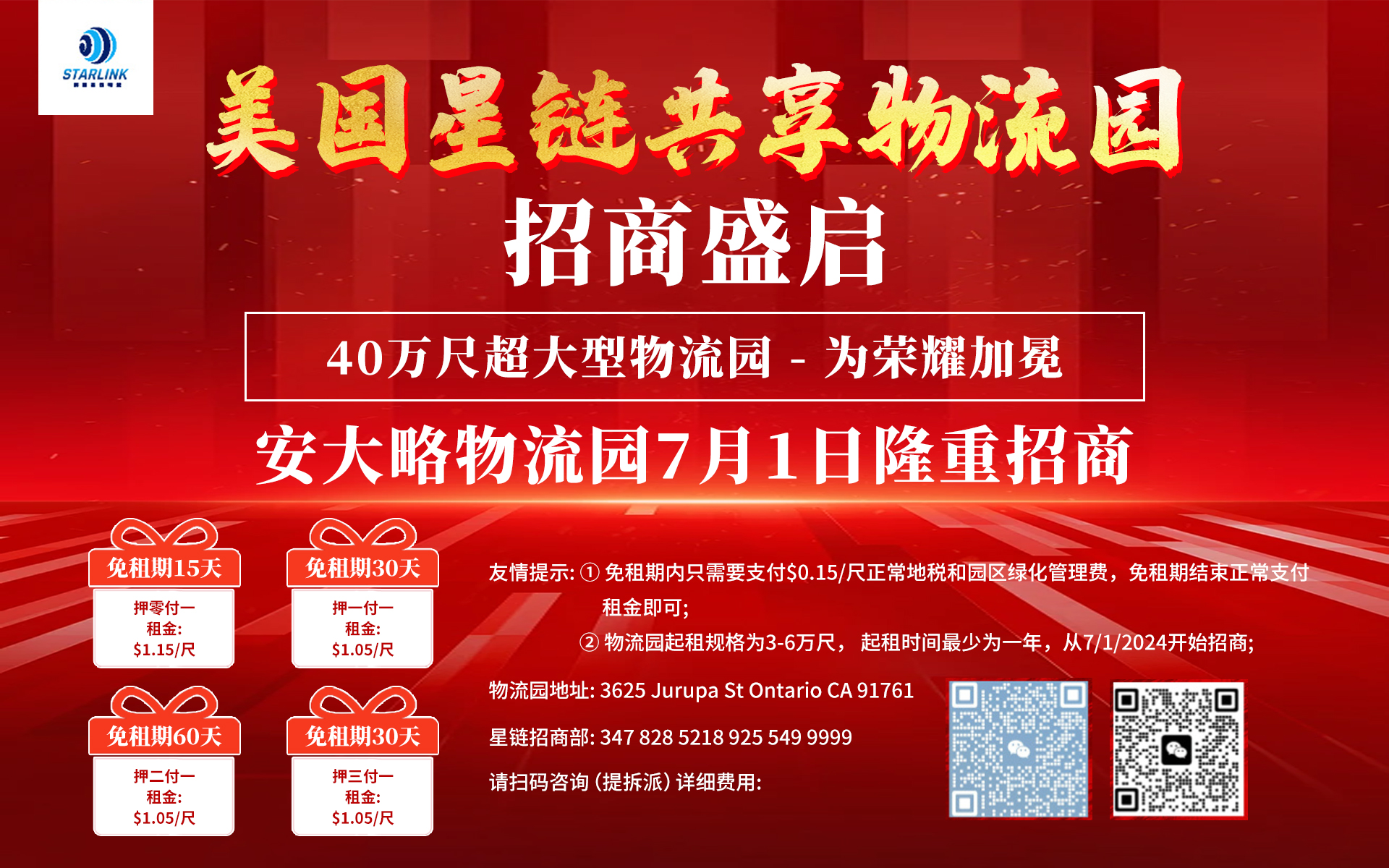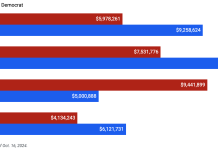【文/托马斯·赖特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乔·拜登已就任总统数月,他的外交政策相较于其国内政策似乎明显不引人注意。这位总统的首要任务显然是应对此次疫情以及推出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刺激计划。然而,人们不应只关注他的国内政策而忽视美国外交政策已发生重大转变这一事实。这一转变不仅始于拜登的前任唐纳德·特朗普,也始于拜登的前老板巴拉克·奥巴马。
构成拜登世界观的关键要素并非显而易见。但你不必去秘密文件中寻找线索,只要听听他说什么就行了。
他在今年2月份说:“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拐点,有些人声称……威权是最好的前途,而另一些人则明白民主至关重要。”在下个月,他对记者说,“依我看”,中国不会实现,“成为世界上最先进国家、最富有国家和最强大国家这个目标。”今年4月,他重申了这一观点,认为世界正处于“民主能否在21世纪发挥作用”这个拐点上。上个月,他对《纽约时报》的大卫·布鲁克斯说得更具体了,“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关注中国的时刻。”很明显,他不仅在正式讲话中这样说,他在平时也总是提起这个话题。
在拜登看来,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正在与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展开竞争。而某一时期的快速技术变革则加剧了这种竞争,使中国获得了在某些领域可能超越美国的机会。
除了发表言论,拜登政府也正与国会展开合作,谋求通过《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以对抗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野心,尤其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野心;拜登政府将优先考虑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关系,而不是美中双边外交;拜登政府还敦促欧洲采取更多措施来对抗中国。
对总统来说,发生这种转变要经历一个过程。两年前,他曾谈到自己为什么认为有关中国实力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并在2020年竞选时说了一句被共和党人抨击的话:“中国要吃我们的午餐?来吧,伙计。我是说,你知道,他们不是坏人。但你猜怎么着?他们还不是我们的对手。”
现在他担心中国是美国的对手了,而且中国不仅仅是对手,中国还可能会赢得这场美中竞赛。这一信念奠定了拜登理念的基础。
对民主党内的许多人来说,拜登转变立场之快令人惊讶。民主党内某些负责制定外交政策的人希望,拜登对中国的看法还没有定型,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和自己的言辞和态度,不再强调美中竞争是民主和威权之间的较量。他们担心美中可能会陷入类似冷战时那样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像2019年的拜登一样,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实力被夸大了,美国可以继续保持耐心和克制。他们认为,虽然华盛顿必须勇于维护本国利益,但它也需要迅速过渡到与中国和平共处的阶段——基本上就是恢复奥巴马政府的做法。
拜登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坦率地讨论了政府的打算,他告诉我,虽然外交决策者们赞同总统的观点,但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和复原派有同样的忧虑,而另一些官员则尚未领会总统言论的要义。
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尤其是德国,也对过于强调抗衡中国感到紧张。拜登在飞往欧洲前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淡化了美国与威权国家间的竞争,转而强调有必要证明民主的有效性,这也许不是巧合。
但所有担心拜登观点的人都忽略了一个拜登早已指出的重要地缘政治发展趋势。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瓦解,两大国家集团正在取代它,一个是民主国家集团,另一个是威权国家集团。双方的行为动机都更多地源自于自己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出于按自己样貌来改造世界的野心。中国及其他威权国家担心,信息的自由流动、民主的吸引力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动摇他们的政权。拜登和美国的盟友担心,中国的企图将破坏自由和民主,将国际规则推向非自由主义的方向,并加强全世界威权国家的实力。
他们的评估都没有错。美国的后冷战体系已间接威胁到了专制政权。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认为这是全球化的有益副作用。
拜登也明白,虽然美国国内的民主危机从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咎由自取的,但它也是更大的国际危机的一部分。只有解决不受限制的全球化、外国干涉选举以及腐败网络这些危机,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更大的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拜登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他正确诊断出了美国当下面临的战略挑战。就像冷战初起时的哈里·杜鲁门和冷战结束时的老布什一样,总统现在也有了一个为新时代建立框架的机会。但这么做并不容易。
在竞选过程中,拜登承诺将召开民主国家峰会。这在当时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为如何推行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具体的思路。然而,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他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局限性。众多民主国家作为一个群体过于多样化;每个国家对总体挑战的评估都有很大的不同。为此,拜登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小型、非正式组织的方式,与个别盟友展开合作。高级官员们相信,你是通过行动来领导众人,而不一定要建立复杂的新机构,至少不用在一开始就建立。
拜登在亚洲打算深化四国机制(QUAD,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集团)在疫苗分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迄今为止,他在与欧洲的交往中缺乏类似的雄心和热情,因为在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的战略评估与他截然不同,默克尔对竞争持谨慎态度并支持欧洲与中国展开接触。美欧这些分歧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
盟友们也在问,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理念能为促进整个自由世界的繁荣做些什么。有人担心,这只是特朗普保护主义的一个较温和版本,拜登也对自由贸易协定持怀疑态度,并偏爱加征关税。拜登政府官员私下承认,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然而,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上周末指出的,七国集团在支持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方面取得突破是一项重大成就,这项政策将惠及全世界的中产阶级,而不仅仅是美国的中产阶级。
拜登的工作之所以复杂难做,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竞争时代与冷战时代有着本质的不同,这要归功于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之间存在高度依赖的关系,这尤其要考虑到中国。拜登必须领导民主国家就如何与中国保持适当接触达成一致。例如,这肯定意味着,在可能有助于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或侵犯人权的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从战略上减少联系。同时,这通常还涉及到管控风险,并在某一盟国遭受侵害时做出集体反应,比如出现了迫降飞机,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惩罚性关税,以及不公正地逮捕其他国家公民等情况。
这种复杂性并不是拜登面临的唯一挑战。如果某一重大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光靠建立非正式组织或专门组织去解决它将是不够的。拜登的外交政策应是与众多志同道合并得到美国朝野上下广泛支持的国家达成国际协议,但考虑到美国政坛的两极对立程度,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样的协议可能涉及遏制和应对经济胁迫行为,建立可靠的供应链或加强对民主和人权的保护。
为了贯彻他的理念,拜登必须在政治上身段灵活。进步人士已纷纷发言,批评他的对华政策,指责拜登总统发动了一场可能激起反亚裔情绪的冷战。但这是一项很奇怪的指控。毕竟,是伯尼·桑德斯效仿温斯顿·丘吉尔1946年的铁幕演说,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发表了外交政策演讲,谴责威权主义。是伊丽莎白·沃伦在参加总统竞选时,把反对贪腐专制主义的斗争作为她核心的外交政策。如果说拜登做了什么的话,拜登也不过是在追随他们的脚步。他应该努力争取将两位参议员都拉入他的阵营。此外,拜登应该提醒进步人士,如果与中国的竞争不是关于价值观和民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针对中国本身,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做法。
另一方面,保守派永远不会在外交政策上完全同意拜登的观点,但一些人正在与拜登展开合作,制定有关中国的法案。许多共和党参议员相信要依赖美国的盟国,并在美国战略中强调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即使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不同意他们的这一立场。一些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表示,如果是为了与中国展开有效竞争,它们将支持建立多边组织。拜登可以利用共和党参议员和特朗普之间的这一分歧,争取两党达成共识,一同支持他外交政策的关键部分。
在美国历史上,有些总统从来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拜登有。在他看来,美国正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展开竞争。他的应对措施不是在枪口下传播民主,甚至也不是促进民主体制本身发展,而是向世界表明民主体制能够发挥作用——既在国内也在国外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拜登能否团结他的政府、整个国家和美国的盟友,将这一主张融入美国的外交政策。
(观察者网由冠群选译自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