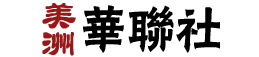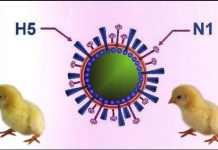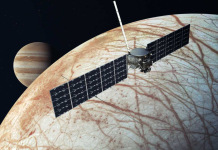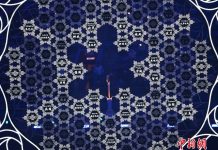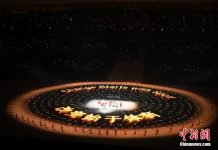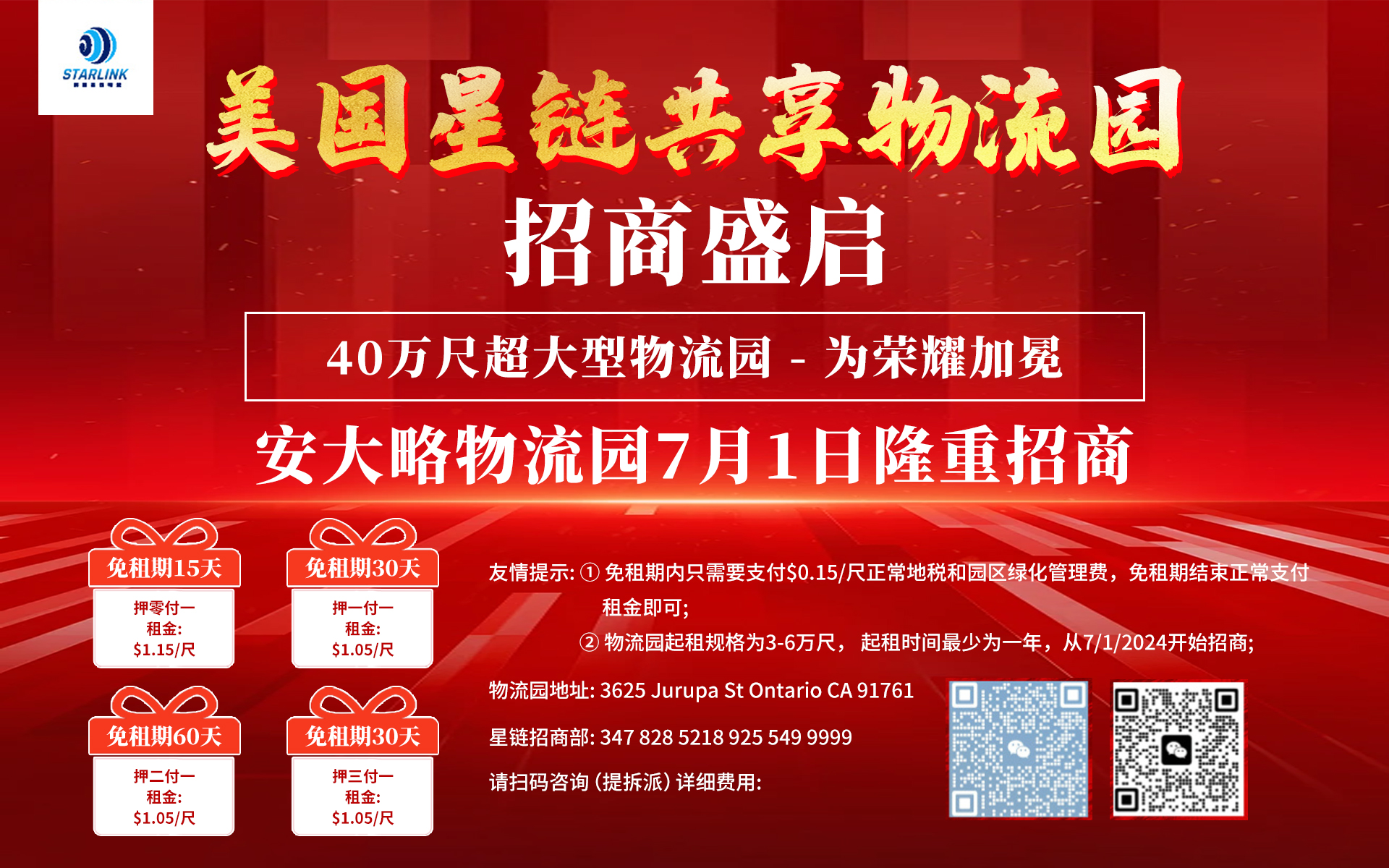中新社北京7月10日电 题:麦家:当代文学为何更是西方了解中国的通道?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静
中国作家麦家正在构思新作,想要探索现代人对感情的认知。从2019年出版《人生海海》后,他就告别了自己擅长的谍战题材。如今,他的谍战作品正在海外走红。
2013年,企鹅兰登以5万美元的预付版权购入《解密》的英文版版权,将其收入“企鹅经典文库”。该文库收录过的中国作家作品仅有《红楼梦》《阿Q正传》《围城》和《色戒》,《解密》成为迄今唯一被收入该文库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且已拥有33个版本,英文、西语译本都跻身当地畅销书榜。

图为麦家。中新社浙江分社记者王刚摄
当年出版《解密》并不顺畅,曾被退稿17次,历经11年才发表。面对今天的成绩,麦家近日在杭州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说,只要人真实地面对自己,充分地表达自己,总有一天自己创建的世界会被人照亮,独到性自然会被他人认可。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您的作品在海外广受欢迎,被译成30多种语言。据说,《解密》还是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作品,被《经济学人》评为“2014年度全球十大小说”,英文版被收进英国“企鹅经典文库”。您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在海外“走红”现象?
麦家:《解密》能够翻译成这么多语种,肯定是不容易的。但它有今天这么好的待遇,也有很多机缘巧合,比方说我就遇到了一位好的翻译,这位翻译的同学恰好和企鹅经典的出版总监是好朋友,就有这种机缘。
遇到了一个好翻译,遇到了一个好出版社,等于“出身名门”。一个嫁入豪门的人,身价就不一样,然后其他语种的出版社也自然会跟上。我觉得这也不是我自己选择的,有时候一本书,就像一个人,它有自己的命。
《解密》在国内出版经过长达十几年的等待和磨难,其实在2002年出版后,到被翻译至国际上,又经历了12年等待,并不是一出来就被人追捧。但我想前提是这肯定是好东西,它经得起一定的等待。

麦家的部分作品:《解密》 《风声》 《暗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因为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您被贴上了“谍战小说家”的标签,还被网友称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父”。您如何看待这个“标签”?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风格?
麦家:我现在的创作就完全与谍战不相关。大家总是在说谍战,其实我写《人生海海》就已经脱离了谍战,写的是农村,写的是故乡,但人家就还是认为我在写谍战。所以一个人要“脱帽”,其实真是比较难。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您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是在1991年,那时候整个80年代的文学热潮已经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大潮。您那时开始写这部小说,而且坚持了11年,当中肯定有各种困难,为什么还要继续?
麦家:按照正常的写作,一个人在这种喧嚣时代面前不可能坚持11年去写一个东西。我一直坚持,是我在现实面前没有那么多选择,写作是童年带给我的一种身体记忆,是我打发闲暇、安放自己的一种方式,它已经长在我身体里。
另外,我写作就是一种生理需要。如果是带着名利心写作,我想一个人不可能经受这么长时间的打击,一转眼整个青春都没有了。我的写作就像有些人喜欢打牌,有些人喜欢锻炼身体一样,那是我的一种生活需要。
还有一个原因,一个人一旦要走向创作,需要的不是一点点动力,而是要有巨大的动力才能推动持续的写作。除了本身有这种欲望,还要对这个世间的某一种人有切肤之痛或者是深切的爱,单单对一个人都不行,这种不会持续,只有对某一个整体有强烈的爱或者恨的时候,人才会去进行创作。比方说,为什么民国的时候有那么多作家爆发出了旺盛的创作力?因为他们对当时的中国、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有深切的爱和痛彻心扉的恨,有强烈的表达欲。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情报机构,遇到一群人,这一群人我至今都还是深深地崇敬他们,我爱他们,也对他们感到同情。由于我遇到了这群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让别人知道他们身上那种高洁的品质以及他们卑微的、凄凉的现实。这是我真正走向创作、持续进行创作的非常具体的原因。

资料图:读者在书架前翻阅图书。 武俊杰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您笔下的那些英雄结局都不太好,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美满一点的结局?还是跟您自己的经历有关?
麦家:跟我的人生观有关系。一个人的结局,不管是生活当中的人,还是我们纸上塑造的人,终归是两个结局,要么喜要么悲,我说了我的乐点特别高,我不能接受一个人最后用一种很欢喜的方式来结局,我觉得那不真实,那不是属于我情感认同的一种结局。
其实我觉得没有绝对的悲和喜:容金珍最后疯了,但是他用这种方式破译了密码,用身体被摧残的方式,解决了黑密的密钥。他疯了,本身是个悲剧,但是密码被破了,又是一个喜剧,悲和喜从何谈起?我写作时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绝对地去看人、看世界,越辩证越真实,也越接近真理。我希望我的读者也是如此。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些人认为让人高兴的作品比较浅,悲剧或者说黑暗一点的作品更深刻,您认同吗?
麦家:我不接受这个观点,不能说苦难的悲剧的东西就深刻,我觉得什么样的作品都需要。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包括现代派探索性的作品都需要深刻。这才是人生,是世界万象,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
对于一位具体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要找到符合自己人生观的调子,你让我去写喜剧或者特别励志的,我可能写不出来,有些勉为其难。但换一个人,让他去写悲剧,他可能也写不好。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写符合自己人生观或者世界观的作品,写作说到底是在自我表达,把内在世界,对人生、对自己的真实认知表达出来就可以。
坦然、真实地面对自己,越充分地表达自己,有一天当自己创建的世界被人照亮,你的独到性就会被别人认可。例如1991年我开始写容金珍这样的英雄人物时,人家不接受,我记得《解密》反复被退稿的一个理由就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家都已经反英雄写小人物了,你还写英雄?”但转眼间时代就又发生了变化,10年过去,读者对那种底层写作、私人化写作已经开始厌倦了,进入2000年后,人们又开始呼唤英雄,一定意义上来说,我的作品是符合了时代、读者的呼唤。这就是坚守的意义吧。

资料图:位于古巴哈瓦那东郊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故居。中新社记者 莫成雄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据说卡夫卡、加缪、海明威、福克纳、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黑塞等,尤其是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对您影响颇深。美国《纽约客》曾评价您“将自己无人能及的写作天赋与博尔赫斯的气质巧妙结合”。这些外国作家给您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
麦家:作家首先是读者,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创作来自于欣赏,如果没有鉴赏能力,没有欣赏能力,肯定不会有创造力。我的写作是一种创造,但在创造一个东西之前,必须要学会欣赏别人,所以阅读大量的作品,各种各样的名著。我觉得这是培养自己的鉴赏与欣赏最便捷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资料图:俄罗斯贝加尔湖,远处两位骑自行车人闯入画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东西方文明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与隔阂,但文学无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您认为好的文学作品有哪些共性?在您看来,文学对促进东西方深入交流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麦家:《解密》能有30多个国家的语言翻译,说明它是世界性题材,我记得《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终于有了一本不需要查字典也可以看懂的中国小说”。
整个西方对中国其实充满误解,充满认知误区。我们的很多小说写的是民俗历史,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不了解,他们在阅读时甚至需要查字典,但《解密》中写到的破译密码是个世界性的职业,破译密码的人物也是全世界特别关心好奇的一群人。因为是世界性题材,我觉得这也是《解密》包括《暗算》走向世界的一个有利条件。
还有一点,中国这些年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越想了解我们,这也是一个大背景。当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的时候,文学是最好的选择。人对一个国家有好感,通常不是通过新闻或政治,而是文学。例如50年代的国人对苏联特别有好感,因为那些年看了大量的苏联文学,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我们了解了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突然会对那片土地充满向往。
我们这一代人就大量看欧美作品,虽然没有去过那些国家,却充满好感。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文学也是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客观、最民间的一种方式。中国现在越来越强,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对中国人的好奇心也在增强,这个时候文学更会成为他们了解中国人的一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