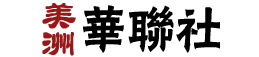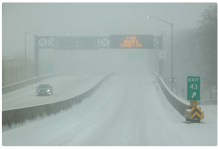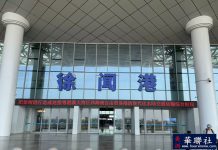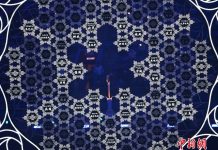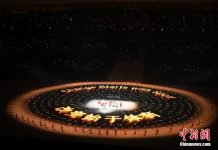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张志强:为什么说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
中新社记者 高凯 李京泽
中国的成长一直伴随着世界关注的目光。自新中国成立起,一些西方政治观察人士就预测甚至断言中国要想发展壮大,将不得不实行西方制度模式。
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全面进步,事实表明虽然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中国并未跟在美欧后面“亦步亦趋”。无论在制度还是文化上,中国都坚持自身特色,没有走上一些人所预测的“另一个西方国家”的道路。
为什么说中国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答案或许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深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指出文明基因的不同使得中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西方,但文明的基因同样让我们不会以西方的方式对待西方。

资料图: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张煜欢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有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讨论文明对一国发展道路的影响,文明基因的概念被讨论得越来越多。应如何在国家发展框架下理解文明基因?
张志强:基因是生物学概念,文明基因是一个比喻。具体到中华文明的基因,应该是指推动中华文明形成的最基本的原型力量。这些原型力量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上持续不断地发挥着作用,保持了中华文明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探究这些原型力量的性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理解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生生不息之生命力的关键。
为什么说文明基因是“力量”而非“因素”呢?因为因素偏于静态,而力量则从动态性着眼。以基因来比喻这种文明的原型力量,实际上是想说明文明有如生命体一样,有一种克服内外挑战、努力实现自身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仅创生了生命,更持续不断地维持并推动了生命的发展。因此,用基因来比喻文明,就是着眼于文明的生命有机体性质。
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在发展过程中克服各种各样的内外挑战,才能让自己的内在目的性得以实现。因此,文明的存续实际上是一个文明自身不断发挥历史主动性的过程。文明的存续与否取决于它能否创造性适应条件、能动性地改变环境,从而推动自身的成长。中华文明长期存续的奥秘,就要从孕育这种历史主动性的基因中去寻找。

资料图: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您能否结合历史谈谈,文明基因如何影响了中国的道路选择?中华文明的显著基因特质有哪些?
张志强:我们在中国和欧洲文明比较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因素,即中华文明是一个文明凝成了一个国家,而欧洲文明,则自从罗马帝国瓦解之后,再没有重建起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尽管在历史上罗马的理想时隐时现,从未消失。欧洲文明最终并没有凝结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在近代形成了一系列民族国家。
严格来讲,只有中国是一个文明凝结成了一个国家,尽管在历史上,这个文明凝结成的是一个有着中心权力的天下体系。相比于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体制,中国的政治体系具有更广阔的规模。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最大的不同点是形成权力的动力不同。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凝聚起更广阔规模的政治体系,是由于其以代表天下全体生民的天的象征赋予政治以正当性,天所象征的天下生民的全体性,就成为大一统政治的根据,而以天的全体性所蕴含的大公至正的价值观和执中平衡的方法论,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根本遵循。
重要的是,大一统不仅是对政治权力集中的描述,更是对天下共同体团结一致的刻画。由天的象征性权威所塑造的政治共同体,是凌驾于基于部分、基于集团、基于阶层的权力诉求之上的。这就保证了天下共同体的政治稳定性,从而也使得“统一”成为天下共同体的基本政治关切。欧洲文明则由于凯撒与上帝的权力二分,导致了宗教不断成为政治革命的动力,从而难以真正维持政治权威的一统,使得分裂成为常态。应该说,这一点是中西文明基因的根本不同。
基于天的象征性权威的中华文明,从天的全体性当中引申出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从天的执中平衡的特性当中引申出了立足全局、虚心实照的“实事求是”方法论,从天下共同体的团结中引申出天下一统的政治追求,这些都以某种文明基因的方式影响着中华文明的道路选择,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基本趋向。

资料图:《旗帜》雕塑。中新社记者 韩海丹 摄
中新社记者: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思潮此消彼长,中国人在积极探索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您认为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过程中,中华文明基因表现出怎样的时代特质?
张志强:中华文明在近代确实遭遇到了一些难题,这些难题一方面是西方的挑战导致的,另一方面也与文明有机体自身新陈代谢机制出了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一些制约中华文明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百年奋斗历程,从根本上突破了这些制约中华文明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从而让中华文明重新恢复了生机。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实际上充分说明了中华文明内在更生力量的强大。而这种更生力量的焕发,正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充分激活中华文明内在力量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历史困境当中积极发挥历史主动性的文明基因。
这种基因是一种不断承弊通变的能力,是一种不断从历史困境中开辟新境界的能力,也是一种将古老文明不断带入新境界、新状态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让中华文明历久弥新、既久且大。在历史长河中,任何文明有机体都不可能一直保持青春状态,但唯有中华文明由于其自我更生的原理,而能够连续发展。
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过程。二者可以结合的前提,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进行彻底哲学革命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哲学精神。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观,也使其具有一种立足全体的人民观。这些精神和思想特质都与中华文明具有内在一致性。二者可以结合的条件,则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实践,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文明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等蕴藏在中华文明中的优秀基因,获得了新的形式,赢得了新的自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突破了许多制约中华文明发展的瓶颈性难题,通过新陈代谢、振颓起弊,而让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历史主动,彻底改变了全体中国人民被奴役被压迫的命运,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

资料图:孔子博物馆内馆藏文物。郝学娟 摄
中新社记者: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其间包括文明交流与互鉴。您认为中西文明有哪些共通性?又有哪些文明基因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
张志强:如果我们回到文明的实际,会发现所有的文明都是有共通性的,都是人在适应各自环境、迎接外在挑战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生活世界、文明世界。如果我们能够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任何文明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那么文明之间是完全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学习的。
从文明历史的实际来看,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各自卓尔不群、漠不相关,而是在多个层次不断发生着横向的互动,在每一种文明的历史横切面上,都可以看到多文明交融互动的层累痕迹。比如,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从中国科举制度学来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科技文明的持续学习,更是中国能够摆脱贫困、摆脱落后的关键。
如果我们保持一种文明交往交融的文明实际观,我们就不会接受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实际上,文明冲突论是一个来自于西方历史经验的假设。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就是一种出自一神论的二元对立观,一种独断论的普世主义。这种一神论的二元对立观是完全与中华文明立足全体的文明实际观截然不同的。
所谓立足全体的文明实际观,总是要求从世界出发理解世界,从他人出发理解自我,强调“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认识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强调“和而不同、不齐而齐”的秩序观,强调“感而遂通”的理解能力。正是这些文明基因,让中国绝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成为另一个“以己度人”“自我中心”“齐不齐以为齐”的“西方”。
文明基因的不同使得中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西方,但文明的基因同样让我们不会以西方的方式对待西方。在当今世界,亟需一种能够从世界整体出发、立足人类命运、包容不同文明的大文明。这种大文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以建立一个全人类共同分享的世界为目的,这种大文明会让所有人、所有文明都能够获得其生存发展的条件。中华文明就是一种具有这种大文明潜能的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可以包容不同的文明,团结全人类,共同创造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新社记者:197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断言,世界的希望在东方,东方的希望在中国,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您认为应如何创造性推进中华文明的当代转化与未来发展?
张志强:应该说,汤因比的说法是有远见的。不过,汤因比的说法还是一种基于他的文明类型比较的推测,而中华文明今天取得的成就,让我们更有底气来阐明汤因比的道理。
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就是对中华文明进行当代转化的历程,我们需要深入理解百年党史的内在理路,全面总结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同时把百年党史放入5000年文明史、500年世界史、200年世界社会主义史的不同历史维度中加以透彻把握,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内在道理。
充分理解了百年党史的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在未来更加自觉地掌握推进中华文明当代转化的历史主动性,只有充分理解了百年党史的内在理路,才会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自觉、更加自信,让全体中国人民更有中华文明的底气、更有中华民族的志气、更有社会主义的骨气。(完)
受访者简介:

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研究》主编。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古典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佛教、明清至近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专长为近代佛学,清代至近代的经史学,阳明学,晚明以来的三教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