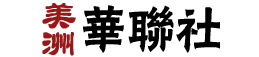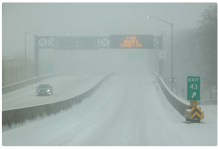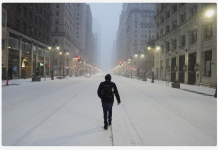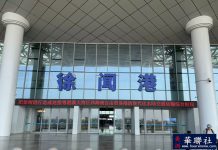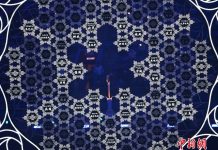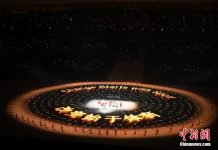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至今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罗大佑的这句歌词,同样可以用到萧红身上。在香港导演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之前,关于萧红的声音,多数只限于文学圈内部;但这部电影之后,各种喧哗之声,关于电影的、文学史的、情感的,一哄而上,几乎到了“无处不萧红”的地步。
在影片上映近1个月、争论渐消之后,香港作家、学者李欧梵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曾友情出演 《黄金时代》(这部分镜头在正式上映时被剪)的毛尖,在思南文学之家进行了一场题为“萧红和萧军”的对谈。因为两位主讲者的专业身份,这场对谈,被认为是“正解”。
问:最“脏乱差”,还是最“黄金”的时代? “
那是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 “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萧红,“想爱谁,就爱谁”的萧军,“想骂谁,就骂谁”的鲁迅……《黄金时代》的系列海报,对“黄金时代”四个字的解读格外吸睛。
毛尖向李欧梵提出了一个很多观众都好奇的问题:上世纪30年代,在历史教科书上可能是一个最“脏乱差”的时代,它怎么就变成“黄金时代”了呢?
李欧梵:我个人感觉,这部电影描述的是我父母那一代。我父母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念音乐系,后来抗战爆发,这些知识分子流亡到其他地方,基本立场都是抗日。这段在电影里交代得很清楚。 电影中有一段让我非常感动,就是这些年轻的作家,到报馆、到别人家借宿。这让我想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当时逃难到另外一个地方,有同事,还有不认识的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家的,他们逃过战乱,靠的就是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文化对他们来说,是精神食粮,不管肚子多饿,也要看书,我父母逃到农村,还拿小本子写日记。“黄金时代”对我来说,体现在共患难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真情,而且是为了某一个理想。 现在来看,那确实是中国文学史的“黄金时代”。 问:作家萧红,还是“三个男人的萧红”? “没有表现出女作家的主体性”
毛尖认为,《黄金时代》的编导显然有一个很大的野心:通过一个女人,来表现她所生活的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但电影的格局,在某种意义上更像“萧红和她的三个男人”,因为经历了这样的三个男人,所以收获了这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对萧红的解释,是电影最被诟病之处。
李欧梵:这部电影的问题是,萧红作为一位女性、一位作家,她的主体性没表现出来,当然这个主体性受制于当时的历史年代。我看萧红小说最大的震撼,是《呼兰河传》一开始,说东北人家的那种大土炕,一匹马都能掉进去; 一位美国学者也说过,萧红的整部《生死场》,就是中国人被蹂躏、特别是女性被蹂躏的历史。女性和贫困是萧红小说的重要主题。 为什么电影不能把萧红小说中最重要的画面(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画面)表现出来,让观众感受到历史和真实?这部电影非常努力,但历史是模糊的,主体性没有出来。 问:负心汉,还是性格使然? “端木蕻良的气派超过萧军” 在“萧红的三个男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军。
毛尖说,最近看了萧军的《延安日记》,感觉萧军“完全是小自我,很‘作。而曾经跟晚年萧军打过交道的李欧梵则说:“我坚决相信他打过萧红。” 李欧梵:我见萧军的时候,他已经是位老人了。他个头很矮,跟电影上完全不同。从他的文章可以感觉到,他有胡子精神(东北土匪),很霸道,而且喜欢跟人打架,我坚决相信他打过萧红。后来我看他的日记,感觉跟毛尖一样,萧军真的是目中无人的。电影里的萧军太像个文艺青年,软软弱弱的,没把他的霸气演出来。 就文学成就而言,萧军是公认比不上萧红的,但端木蕻良的成就很可惜被忽视了。我个人对端木的感觉是,他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作家,他写的《科尔沁旗草原》,在气派上超过萧军,甚至超过萧红。夏志清先生就特别推崇他,但在电影里面完全看不出来。
问:鲁迅是导师,还是更复杂? “
先生也有所谓的‘中年危机’” 毛尖指出,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与汪曾祺的《我的老师沈从文》,被认为是现代最好的两篇回忆性文章。但从萧红同时代作家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萧红与鲁迅关系的另外一面,比如萧红经常跑到鲁迅家中,一坐就是半天,许广平曾向朋友抱怨萧红的不通人情世故。 霍建起导演的《萧红》中有这样一幕:鲁迅告诉萧红,为她小说做的序写出来了,然后问:“你拿什么谢我?”这段处理被毛尖认为“很邪恶”,但曾推出《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 的李欧梵则认为,不妨还原一个更有血有肉的鲁迅。
李欧梵:要是让我在电影中处理鲁迅与萧红关系的话,我会把镜头放在这样一幕场景—萧红穿了一件新衣服过来,鲁迅讲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可能有错误,可能对鲁迅不敬。鲁迅那时五十多岁,看到年轻、尽管不是那么漂亮的女性,还是有一点特殊感情的。鲁迅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所谓的中年危机,但是电影可能受到拘束,没有把这一块表现出来。
问:抛弃孩子是狠心,还是无奈? “
这是当下的人没法切身体会的” 在对萧红的各种批判中,有一种说法认为,萧红作为女性,作为母亲,竟然几次轻易抛弃自己的孩子,连最起码的责任心都没有,何谈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 之前毛尖曾撰文指出,如果有所谓的“黄金时代”,那也是萧军的,不是萧红的。不过,在活动现场,毛尖坦言“当时写这个话不是特别慎重,萧军的家人提出来,如果有黄金时代,那也不是我们萧军的”,但她同时认为,“相对来说,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一个自由度的话,萧军的还是要比萧红广阔一些”。
李欧梵:我是1939年出生的,弟弟妹妹晚4年出生,是一对双胞胎,但弟弟不到两岁就死了。当时的环境非常困苦,我母亲是音乐教员,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家累得不得了。我弟弟因为吃坏东西而死,他们就草草埋葬了这个孩子,过几天照样生活。你能说他们不爱这个孩子吗?不是,他们是认命了。在当时情况下,很多个人的基本欲望都在重压之下,没有办法实现。 电影中,三个人睡一张床,年轻的观众看着觉得很开放,很先锋。实际情况是,那是万不得已,而且他们都是穿着衣服的。当时那些人受的困难,现代人是没有办法想象的,特别是女性。这里面牵涉到女性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变成历史条件下的,她们主体性的表现肯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 个人的满足、人性的张扬,这是一个小康时代的要求。在一个战乱时代,能够活下来已经不简单,什么是苟活?什么是为理想而活?这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没法切身体会的。很可惜电影没有表现出来。 – See more 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