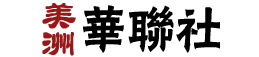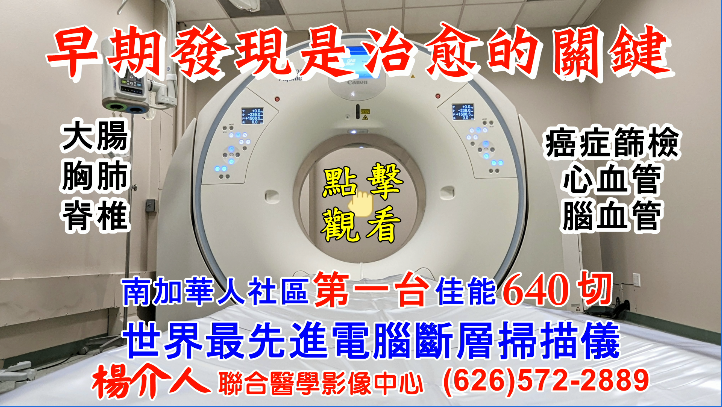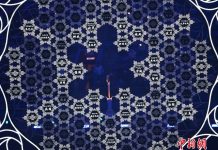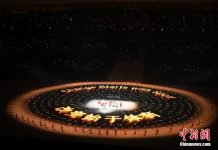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 …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拥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增加了一个挑战性因素,因为这意味着,没有践行这些原则的政府不完全具备合法性。” “这一信条——太深植于美国人的思维中,以至于时不时会被当成官方政策提出——暗指,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某种不尽人意的试用性安排中,有一天将得到救赎;在此期间,他们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关系,一定会存在某些对抗性元素。” 这是美国卓越的地缘战略思想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我曾在他领导的国务院任职)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写道的。
我们在美国现任国务卿克里11月4日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的演讲中,就听到了基辛格所指出的这种自负。 这次SAIS演讲发表于克里启程踏上赴北京参加APEC会议、陪同奥巴马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旅的前夕,因此被宣传为关于美中关系的重要声明。 很多观察人士,包括我自己,原本希望该发言将预示着中美关系“重置”——这种重置是需要的:很多客观分析认为,美中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执政6年间有所恶化,现在已是10年来最差状态。 但“重置”却没有发生。相反,克里详加解释的,是一种盲目乐观、不真诚选择、巧妙寻衅、间或屈尊俯就、绝对轻蔑的“打定主意”和“坚持己见”,为美国维护地区军事霸权“一切照旧”做辩护。最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拒绝与中国在亚洲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克里说,“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有深远重要性的。它将在决定21世纪形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对的事情。而这就是奥巴马总统从首届任期开始就聚焦的事情。”
克里11月4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演讲 克里以“要做对的事情”解释了奥巴马的再平衡政策,这种缺乏洞察力令人瞠目但显然也是一种自然流露。克里说明了四种政策“目标”:一,最终敲定TPP(当然不包含中国);二,实施新能源政策应对气候变化;三,通过加强机构和规范减缓紧张并促进区域合作;四,使整个亚太地区的人民得以过上有尊严、安全和机会的生活。
谈及与中国的“不同”时,克里转而使用了一种特别且更严厉的语调: “… …当我们提到管控分歧,那并不代表我们赞成意见分歧”,相反,美国一直并且也将继续坦率、坚定地实践我们的特权:保护自己的利益、必要时挑战中国,比如在“海上安全方面,尤其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 …网络窃取商业秘密”,以及“香港局势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权问题,因为尊重基本自由现在且一直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 …” 克里说,“我要明确指出,美国在清楚表达我们的价值或维护我们在整个地区的利益、我们的盟友,以及我们的伙伴方面,永不退缩。”
在此之后,克里热情洋溢地、在我看来却既无说服力也不真诚地大谈他所看到的美中“伙伴关系”和联合“领导”前景。 克里所说的“完美的例子”是“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威胁的努力”,在此方面两国拥有“共同责任”。他以一种很容易被视为居高临下的态度表扬中国,认为中国为对抗埃博拉疫情做出1.3亿美元承诺以及计划派遣解放军赴非洲支援,这体现了“全球领导力”。 同样居高临下的,是克里关于在非洲、中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协调… …援助和发展工作”的讲话:“如果我们确保我们的措施是无偿的、协调一致的…(以)帮助数百万家庭脱离贫困… …”
在此之后,克里的谈话,就像一架减速的飞机无法保持高度一样,陡然转为说教“人民对人民交流”的价值。 美中关系最重要、紧迫及潜在危险的话题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 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CMSI)副教授莱尔·J·戈尔茨坦(Lyle J. Goldstein)10月29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所称:“… …我们都应该对美中关系中现已完全可见的、明显不稳定的军事竞争,感到充分不安”;“没有将美中关系置于稳固基础之上,(一直是奥巴马)政府外交政策的明显失败… …”
不管克里的措辞如何,这一直都是美国的政策,尤其是以军力为焦点、受五角大楼驱使、瞄准中国的压倒性“再平衡”政策——其军事行动强调“加强联盟”对抗假想的中国威胁,因此激起了既挥霍又危险的军备竞赛,那一直是、并将继续是美中关系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不过克里讲话最令人失望和痛心的,是他无疑蓄意遗漏了提及寻求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件事。
通过这一遗漏,克里非常清楚地释放出信号:美国将不会参与这一计划(观察者网注:指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反,美国的政策是,保持美联合盟国建立起的军事霸权这一区域地缘战略现状,尽管美国意识到,这种现状对中国来说具有潜在威胁性、且从长远角度不可接受。 这预示着——至少在奥巴马余下的总统任期内——两国关系仍将处于战略僵局和不稳定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