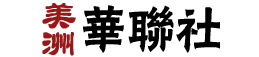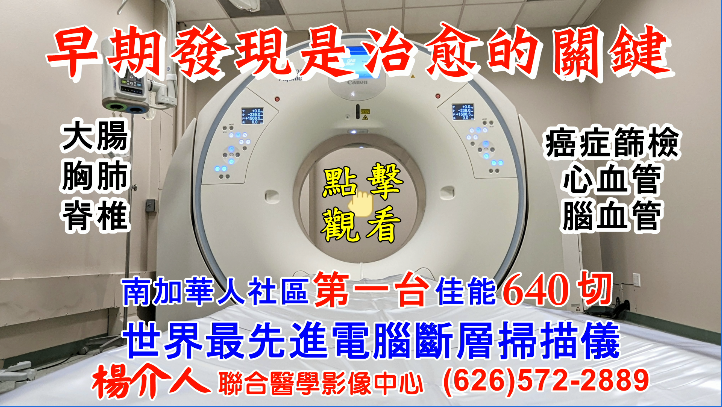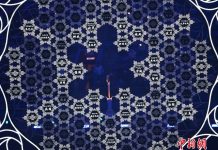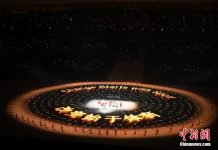199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撰文,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他指出,冷战结束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将成为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该观点在国际舆论界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本文以文明冲突论为切入点,探讨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最终在于说明文明的交往。
一.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认为,冷战后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伊斯兰文明。伟大的宗教是伟大文明建立的基础。亨廷顿所谓文明间的冲突主要是宗教间的冲突。暂且不论亨廷顿理论的正确与否,从历史上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确实有过多次的冲突与斗争。公元7—8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崛起直接威胁到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地位,而11—13世纪的1东征更是对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关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并且留下了双方怀疑与斗争的历史遗产。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西方对穆斯林世界内部事务诸如阿以冲突、海湾危机、伊拉克问题等等的频频干预,从而引起穆斯林世界的强烈不满。直到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与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对立情绪依然存在。
美国是基督教文明的典型代表,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教的诞生地和麦加、麦地那两圣地的护主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文明的冲突在这两国之间同样存在,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然而,从1945年以来,沙特与美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自1945年沙特开国先王伊本·沙特与罗斯福总统在”约翰·昆西”号巡洋舰上会晤后,两国就确立了”石油换安全”的合作模式。沙特为美国提供石油,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护。同时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领域广泛合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从1933—1980年,美国阿美石油公司一直主导着沙特的石油开发,直到80年代沙特石油国有化。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政策不是基于共同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因素,而是以实实在在的战略利益为基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基于战略利益的需要结成现实的联盟,这对当政者来说,不啻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然而,受宗教情绪的影响,两国民众的宗教非理性因素往往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羁绊,尤其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借助1手段进行反美活动,对沙美关系造成重大影响。
沙特王室的亲美政策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王室的借口,1979年发生的麦加大清真寺被占事件即是一例。1979年11月2日,以朱哈曼·本·沙伊夫为首的一批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武装占领麦加大清真寺。朱哈曼宣称他的内弟穆罕默德·卡赫塔尼正是人们期待的马赫迪,号召在寺内祷告的穆斯林起来推翻投靠美国的、腐败的、非伊斯兰的沙特家族的统治。[1]118以沙伊夫为首的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力图诉诸宗东政治与国际关系。通过伊斯兰教的力量为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性外衣,达到推翻沙特王室的现实目的。虽然叛乱最终遭到当局镇压,但是沙特国内的反美主义浪潮并没有就此平息,它就像潜伏的暗流,一遇到合适的机会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海湾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队驻守在沙特,很多穆斯林认为此举亵渎了宗教圣地。战争结束后,美军直接驻扎在沙特,为其提供安全保护,防止邻国侵犯,维护沙特王室的家族统治。驻沙美军遭到沙特多数人的反对,沙特宗教反对派更是以此为契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及宗教理念,其中以乌姆库拉(Umm al-Qura)大学伊斯兰学院的院长萨法尔·哈瓦利(Safar al-Hawali)博士为代表。他公开发行磁带,矛头直指政府,批评政府在海湾战争期间与美国”恶魔”结盟,反对穆斯林兄弟。萨法尔·哈瓦利说,邪恶之所以会降临到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是因为他们的人民及王室”误解”了伊斯兰教。”不是世界在反对伊拉克”,”是西方在反对伊斯兰教”,”如果伊拉克占领了科威特,美国占领了沙特阿拉伯,真正的敌人是西方,而不是伊拉克。”[2]63-64沙特宗教反对派的伊斯兰兄弟情结超越了国家间的冲突,他们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归为穆斯林之间的内部事务,排斥美国人的干预,而忽略自身的国家安全。这种伊斯兰情结的排外性无助于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当然遭到沙特王室的拒绝。
如果说沙特一部分人对美国的不满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话,伊斯兰极端分子则对美国发动了直接袭击。1995—1996年,美国驻沙特军事基地先后发生两起爆炸事件。一个自称为伊斯兰改良运动的组织及自称为”海湾猛虎”的组织宣布对这两起事件负责。他们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要求所有的”十字军”撤出阿拉伯领土,结束沙特王室的统治。[1]118这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沿袭了中世纪穆斯林对基督徒的称呼,试图将两者之间的矛盾扩大化,以获得更多穆斯林的支持。极端分子的所作所为,其实质在于,以驻沙美军为靶子,以推翻沙特王室为目的,建立一个纯粹的、不受西方尤其是美国影响的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社会。对美国人的攻击成了极端分子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方式、一种手段,文明冲突的表象被其利用而具体化、实际化和目的化。伊斯兰极端分子所采取的一系列报复措施严重威胁了驻沙美军的安全,然而,重重0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沙美亲密关系,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依然故我。极端分子对美国的袭击并没有结束,一小部分人加入国际恐怖组织,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1者”一道,对美国进行恐怖活动。美国”9·11″事件即是一例,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绝大多数被认为是沙特人。
沙特极端分子的这些反美举动都是对美国人仇恨心理的反映、报复和发泄,具有宗教意义。宗教成了对美国开战的工具。宗教被视为真、善、美价值的源泉和最高精神象征,宗教离人的心灵最近,煽动宗教狂热可以使天性善良的人丧失理性,做出许多有悖于宗教主旨的事来。宗教价值的超越性更容易使人走向极端,因为安拉是不谬的”超然存在”,以安拉的名义对恶人开战成为宗教虔诚的体现,它天然就是正义的和合理的。[3]极端分子在对美国的报复中找到安慰、自信和力量,同时也向基督教世界表明了伊斯兰教的优越性。
沙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行为是暴力的、极端的和不合情理的,是宗教情绪极端化的表现。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则能够从理性的角度对待本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不同和差异,择其有利者为我所用,不利者则弃之。沙特政府积极与美国进行军事、外交及经贸上的合作,在文化价值观上则恪守伊斯兰的主旨,抵制西方的民主制度。前国王法赫德曾明确表示,民主制度不适合沙特。1992年3月28日,法赫德国王在对阿联酋《团结报》发表的谈话中说,沙特不能引进不适合本国国情的西方制度。他强调说,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多党民主体制,这些体制并不符合本地区和沙特人民的情况。他还说,伊斯兰是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伊斯兰法才是我们的完整宪法。[4]文明的冲突是存在的,关键在于人们的态度及做法。伊斯兰极端分子扩大沙美之间的冲突,将其具体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沙特国家领导人则能够超越这种冲突,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正如沙特普通民众对美国不满一样,美国国内同样有人对伊斯兰文明存有恐惧和偏见,往往把一小撮分子的活动等同于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
1993年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的0事件和1994年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劫持法航客机,这些都加深了美国和西欧对伊斯兰威胁的恐惧。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间即将发生冲突的说法在美国的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中广泛流传。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对沙特的偏见扩大化,将一小撮极端分子的活动等同于沙特普通民众。兰德公司在呈送给五角大楼咨询委员会的一份简报中将沙特阿拉伯描述成美国的敌人,”沙特人在恐怖链条每一节上活动积极,从策划者到资助者,从干部到普通士兵。”[5]美国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沙特的情绪。美国主流思想界指责伊斯兰教”狭隘”、”排他”、”不宽容”、”政教不分”、”不接受现代性”、”落后”、”歧视妇女”,基督教右翼一些代表人物竟然公开攻击伊斯兰教为”邪教” 。”9·11″事件的阴影遮蔽了美国人的视野,使其将极端分子的范围扩大化,这是感情受到重创后所作出的非理性反应,并不表明文明的冲突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主线。
二.利益的诉求
从国家层面来说,尽管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对沙特和美国来说,至关重要的战略关系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至今,沙美特殊关系已有60年的历史。冷战前,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具有政治经济双重意义。冷战期间,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密切合作,共同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反对阿拉伯激进势力的扩张,同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广泛合作,双方结成了战略合作关系。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在美国安排下,拟由埃及和叙利亚出军队,海湾六国出钱,欲构建海湾地区”6+2″安全体系。但是,沙特阿拉伯担心此举会威胁到自己在阿拉伯半岛的领导地位致使该计划最终流产。但同时沙特也坚信:同美国的安全联系及其他的国际安全协定(如联合国领导的主要大国在伊拉克科威特边境的维和行动)是最值得信赖的,也是最有效的保护方式。美国成为最佳的借助对象。[6]冷战结束后,美国掌握了海湾事务的主导权。它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政策非常清楚:遏制两伊,防止地区强国向自己的支配权提出挑战,同时保证国际市场石油供应,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7]在此目标下,美国需要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海湾地区大国,利雅得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这涉及石油、地区安全等问题,在反恐问题上,美国也需要沙特的合作。因为,沙特可以凭借伊斯兰世界精神领袖这一身份,在情报及切断1财源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沙特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基石。
海湾战争确立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美国在海湾地区构建了以自己为主导的安全体系,沙特阿拉伯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后冷战时代,海湾地区更加动荡不安。沙特视伊拉克为”潜在的地区性大国”和对手,是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非常警惕伊朗在海湾地区的霸权野心。一直以来,沙特与也门矛盾重重。红海对面的苏丹支持世界各地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活动,为世界各国所担心。现在,虽然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美国推翻,但沙特的安全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善,伊拉克动荡不安,极端分子在伊拉克活动猖獗,对任何邻国来说均是不安全的因素。鉴于沙特国富军弱,目前,在安全事务中的自立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沙特安全唯一可靠的选择就是同美国的现实安全联盟。[2]87沙特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驻军,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家族统治,抵制邻国侵犯,双方形成了一种”战略盟友关系”。
在该框架内,双方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领域继续加强合作,特别是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极为重要。当今世界,1的概念扩大,它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边疆安全,而且包括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非对称性对抗,后者表现为国家与1、0主义、极端主义的非常规战争。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对美进行1活动,对美国构成巨大威胁。沙特阿拉伯作为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及资助大量伊斯兰组织的举动,使其在打击伊斯兰1分子的行动上能够发挥特殊作用。在美国压力下,沙特在2002年12月宣布采取一系列反对1的措施,如切断1分子的财源,对穆斯林世界正在发生的”思想战”做出回应等等。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间的非正式结盟关系已经持续了60多年。尽管双方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彼此的利益需求使它们走到了一起。
实践证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在利害关系冲突无法调解时可兵戎相见,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的国家在共同利益需要时可联合抗敌,美国与沙特的合作关系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8]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基于利益的需要而结成现实的联盟这对双方来讲是一种”双赢”的战略选择。虽然,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斗争的历史时常像幽灵一样漂浮在两国民众的心中,成为两国关系的掣肘因素。但是,在国家关系层面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文明间的冲突。
三.文明的交往
沙美之间文明的冲突,从表面上看,是宗教政治文化方面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的碰撞或选择,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不同文化观念的人。拿沙美两国来说,一般民众对对方宗教文化传统持排斥态度。这固然有一些认识论的因素在作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治及经济利益的矛盾。譬如,沙特王室之所以一直拒绝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举行西方式的议会选举,就在于一旦这样做,沙特宗教反对派凭借着深厚的宗教传统必将取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很难预料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一方面,这对沙特王室来说,不仅王位不保,王室的经济利益必将大大受损。如1990年2月,沙特妇女做了一次大胆地试验,即自发地在利雅得大街上开车以要求更多的自由时,沙特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谈论民主对自己的统治来说是多么危险的事情。[9]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保护沙特王室是美国的利益之源,美国当然不希望沙特政权作任何改变,以免威胁到自己在海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一直以来,华盛顿急于在全球推行民主。克林顿当政时期,以此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克林顿政府曾经支持卡塔尔、阿曼和科威特的妇女选举,呼吁正在同1事分子作战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为其人民广开言路,同伊斯兰1者对话,支持摩洛哥和约旦国王吸收反对派进入政府和国会,并且花大力气支持也门的民主改革,希望此举能够激发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同样的改革;但是,当涉及到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利益的核心———埃及和沙特时,美国却无所作为。
克林顿政府满足于沙特远离这些麻烦,只要沙特能够继续支付巨大的武器账单,购买波音飞机,保持合理的油价,允许美国使用沙特的空军基地等等。因为,美国知道沙特的任何革命将给美国在中东至关重要的利益以毁灭性影响。一旦旧政权0,将对美国的1产生难以接受的威胁。[9]自2003年起,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造伊斯兰世界,欲建立中东新秩序。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的关系受到新的冲击。
沙特调整国内政策,主动迎合美国,初步进行一些民主化尝试。当年,前王储现任国王阿卜杜拉提出阿拉伯改革计划,此后,沙特允许在本国建立第一个1组织。2004年初,沙特政府举行市政选举,吸收50%的市政委员。在美国改造中东战略的压力下,沙特阿拉伯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迹象;然而,两国的双边战略关系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需要沙特的石油及中东地区一个稳定的伊斯兰盟友,而沙特也需要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保护,双方互有所需。美国1大谈民主在中东的好处,却对沙特的自由选举没有兴趣。除了英国和以色列外,没有一个外国政府像沙特阿拉伯那样在外交和私人关系如此接近于布什政府的”心脏”。
故而,沙美之间虽然有文明的冲突,但是,巨大利益的存在使这种”双赢”的结合,超越了冲突的界限。明的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冲突的最终结果是走向融合。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其基本途径是在本土文化基线之上的交融整合,即取长补短,转化集成、宏观继承、综合创新。[11]对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来说,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