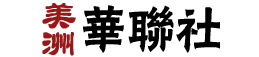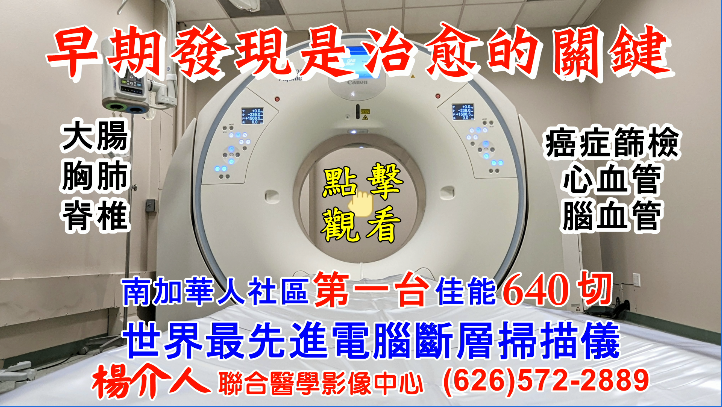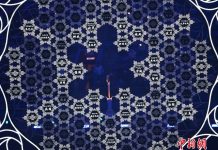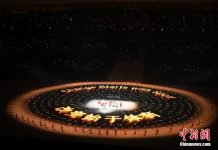茶,可以非常自豪的定义为国饮。品茗啜香,显然不是饮茶这么简单,而是修身养生,平心静气的文化事儿。我经常受邀到朋友家中或茶室品茗喝茶。邀请者往往好茶招待,并以茶艺或茶道标榜,但在我心中,总觉得少了一些文化的味道。
茶文化的核心,一定是文化,但社会上普遍认为是茶艺和茶道。所谓的“茶艺”来自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当时,台湾的商业推起了一股茶文化复兴浪潮,各种茶艺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茶艺”一词标榜饮茶的艺术,讲究茶叶的品质、冲泡的技艺、茶具的精美。通俗地说,就是泡茶技艺的化妆词,并无文化的内涵。而茶道,早已失去了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仪程,仅仅是日本茶道的名词套用。
复兴中国茶文化,总应该有个被复兴的标杆吧?以我的研究发现,最值得我去推荐的是清朝的饮茶风俗。清朝的饮茶风俗,是真正中国茶道艺术的完成及进入到风尚形成的阶段。因为中国人的饮茶从烹茶、煎茶进入到了饮啜和品“味”形式和层次,既是茶道艺术的延伸,同时又是茶文化体现的起点。清朝的饮茶雅趣和宫廷、文人的品茶风尚以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足以成为我们今天复兴中国茶的标杆。
在清朝,饮茶品茗有非常多的清规戒律,和定义明确的“所宜”、“所忌”之事。清初,一直隐居不仕的前明遗老冯正卿,在其所著的《芥茶笺》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他提出了饮茶品茗的“十三宜”和“七禁忌”。所谓“十三宜”是指可以喝茶的理由,共计十三项:第一是无事。要有闲暇工夫和品茶的时光;第二是佳客,饮茶的客人必须是高雅博学之辈,既能与主人交流感情和对话,又能真正品玩茶之真味;第三是幽座。追求环境的清幽雅适,使饮者怡神自得;第四是吟咏。品茗的时候,饮者能低吟高唱,以诗助兴,或与客对咏,以诗文唱和;第五是挥翰。饮茶的时候需要挥毫洒翰,泼墨诗画,以尽茶兴;第六是徜徉。古院幽深,闲庭信步,时饮时啜,体验古之饮茗者的闲情兴味,必将趣味无穷;。第七是睡起。古树下,小径旁,饮者一酣清梦,小睡再起,重品香茗,则另有一番情趣;第八是宿醒。饮者如宿睡未解,醉意矇咙,则稍饮美茗,定能破之,神清意爽;第九是清供。品茶时宜有清淡茶果佐饮,以供啜茗食用。第十是精舍。饮茶时宜有精美清幽而雅致的茶舍,以便能更好地衬托和渲染出肃穆、高雅的气氛;第十一是会心。品茗时,贵在饮者对饮茶艺术、茶的品味和茶道本身的心领神会;第十二是赏鉴。饮茶时,饮者需能真正品玩和鉴赏茶之真味,领悟其中的意境和艺术真谛;第十三是文童。饮茶时宜有聪慧文静的茶童,随侍身边,以供茶役,以澄清寂。
饮茶品茗也有很多的禁忌,其中的七项就是所谓的“七禁忌”:一不如法。即茶水的冲泡都不得法;二是恶具。饮茶与烹茶最忌茶器、茶具低劣,粗恶不堪;三是主客不韵。饮茶是个高档的文化事儿,忌讳客人举止粗俗鄙陋,没有风流雅韵;四是冠裳苛礼。饮茶之事,乃消闲品茗之道,所以不需要官场交往陈规琐礼和使人拘泥的着装打扮;五是荤肴杂陈。饮茶品茗贵在清心安逸,茶如果混杂荤腥之味,茶点如果是荤素杂陈,会破坏了茶味,导致饮者兴致顿消;六是忙冗。喝茶品茗最忌繁忙冗杂,心绪紊乱,神不守舍,既没有细品茗茶的工夫,又没有消闲的雅趣;七是壁间案头多恶趣。喝茶品茗的时候,为营造饮茶主客心绪雅适,所以不能出现墙壁上或座椅案头布置粗俗不雅,使人感到环境恶劣,毫无情趣。
饮茶品茗不仅是文人的雅事,在京师紫禁城内,皇帝与宫中的帝后日常生活中,也以饮茶品茗为雅趣乐事。宫廷的喝茶品类中有奶子茶、绿茶、花茶等,并佐以茶食糕点。据清宫文献记载,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别喜欢龙井新茶。杭州龙井新茶以采自谷雨前者为上品,称为雨前茶,采摘于清明节前的称为明前茶,进贡为头纲。乾隆皇帝还喜欢的就是宫廷御制的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并有诗文记载:“茶宴日即赐此茶,茶碗亦摹御制诗于上。”
清代的文人雅士,以嗜茶为高雅之事。他们借助品茶,作诗唱赋,挥毫泼墨,大发雅兴或自视清高,退隐山林,烹茗饮茶,以求超脱;或邀友相聚,文火青烟,慢品名茶,推杯移盏,以吐胸中积郁;或夫妻恩爱,情深意切,文火细烟,小鼎长泉。花前月下,品茗共饮,以诗唱和,不一而足。从而引出诸多或喜或悲、或感或乐、或慷或慨、或聚或离的人间故事与情话。
“董小宛罢酒嗜茶”就是清初江南才子冒襄与名妓董小宛二人通过饮茶品茗而引出的动人的爱情故事。而清初顺治时,江苏丹徒张则之,是江南名士,他一生嗜茶,并且已经成癖。古籍中记载他“出入陆氏之经,酌古准今,定期不刊之宜,神明变化,得乎口而运乎心矣。”而且他烹茶品茗的时候,最擅长“别水性”,如果外出前往其他地方的时候,一定要自带经过自己鉴定过的水,才能与他人烹茶同饮。
茶文化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内涵体现,谈中国茶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外化,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及天、地环境的兼容,构成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来表现出礼节、人品、意境、美学观点和精神思想的统一。
李建军写于中国文化研究会
2016年10月6日北京